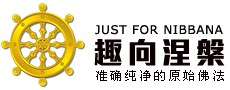何来有我-佛教禅修指南
Who Is My Self?
A Guide to Buddhist Meditation
The Potthapada Sutta
The Buddha’s Words on Self and ConsciousnessInterpreted and Explained
by
Ayya Khema
艾雅 柯玛 讲述
果儒 译
《布咤婆罗经》是记载佛陀回答布咤婆罗有关自我和意识等问题的开示;此书系作者对《布咤婆罗经》的诠释和解说。此书对修行的次第和四禅八定也有详细的说明,是非常好的禅修指南。
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生命的意义时,人类似乎已进入新的历史。在过去,人们追求幸福的家庭生活、宗教、政治和职业,认为这些可以使生命更圆满,即使这些愿望不会挂在口边,却在每个人的心中。
今天,以往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早以摇摇欲坠,难以作为有意义的生活的基础。假如我们认为,只有二十世纪的人类才知道追求生命的意义,当我们读了《布咤婆楼经》佛陀的开示后,就知道我们错了。
经中有一位叫布咤婆楼(Potthapada)的外道,向佛陀请教许多有关自我(Self)和意识的问题。佛陀煞费苦心、不厌其烦的为他解说,给他正确的指导,教他如何修行,以证得最圆满的解脱,这段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对话至今依然中肯贴切。
我们也会读到布咤婆楼的朋友和伙伴们不同意这些新的想法,并想使他放弃对佛法所产生的兴趣,这现象至今依然如此。
我希望借着对这部经的解说和诠释,使这部经变得生活化,并为读者们指出方向,使读者在修行中发现生命的意义;而所有找到内心的平静、喜悦和满足的人,希望他们对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能有所贡献。
本书内容来自一个为期三周的禅修营中的讲座,地点在美国加州,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五、六月。
由于Gail Gokey和Alicia Yerburgh的慈悲、慷慨和参与,让我们能读到这些有助于修行的文章。我个人非常感谢Gail和Alicia的辛劳,也感谢Toni Stevens,他很善巧的安排这次的禅修营;也很感谢Traudel Reiss在电脑方面的帮忙,使编辑及校对得以顺利进行;在Tim McNeil干练的领导下,智慧出版社为本书设计精美的封面, 而我也很高兴能名列出版社的作者群之中。
如果本书能使那些修行人对佛法更有信心,更喜欢修行,能获得更高的内观智慧,得以观察究竟实相(absolute truth),那么所有为本书流过汗水的人都会感到非常欣慰,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付出我们的时间和爱。
在修行的过程中,在解脱道上,我们都具有开悟的潜能,愿此书成为禅修者的良伴,愿正法常住人心。
艾雅、珂玛 于德国.佛陀精舍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第一章
修行的起点:持戒
上座部佛教以巴利三藏作为佛陀教法的基础,巴利文是由梵文演变而来的,为佛陀所使用。两者的不同正如拉丁语与意大利语。在当时,学者们会说梵语,而一般大众则会说巴利语。佛教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巴利三藏又称为Tipitaka,Ti是三的意思,pitaka意为篮子。三藏包括律藏(Vinaya),记载比丘及比丘尼的戒律;经藏(Suttas),记载佛陀所说的法;论藏(Abhidhamma,阿毗达摩),是佛教较高深的教理。为甚么称为三个篮子呢?因为最初的经文是写在干燥的香蕉叶上的。干的香蕉叶颇为坚实,将经文刻在叶子上,再涂上特制的草莓汁,再将其他部份抹掉,就会留下黑色凹陷的文字。直到今日,斯里兰卡的某些寺院仍用这种方法来复制经文,当旧的叶子毁坏时,僧众会把旧的叶子中的经文抄录在新的叶子上,这些刻有经文的叶子会用很厚的木板放在叶子的上下方,然后捆绑起来。有些施主会用金或银装饰的木片,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这些贝叶经并非书本,无法用一只手拿着,通常这些贝叶经会放在三个篮子里,以便携带,所以巴利三藏又称为Tipitaka或三个篮子。
此书从开始到结束都在讨论一篇英译的《长部》(Digha Nikaya)第九经经文。Digha意为长,Nikaya意为部。佛陀入灭多年后,他的开示被结集成五大部类的经典,分别是《中部》(Majjhima Nikaya、《长部》、《增支部》(Anguttara Nikaya)、《相应部》(Samyutta Nikaya)和《小部》(Khuddaka Nikaya),不适合归入前四部的经典,则收入《小部》。
《长部》经文包括整套的修行方法。我们必须知道佛陀在两个层次说法,一个是相对的层次(relative truth),另一个是绝对的层次(absolute truth)。刚接触佛法时,我们对绝对层次的法没有概念,若碰到绝对层次的法(truth),可能会退缩,因为同一个问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讨论,会有不同的答案。例如,我们听了一个禅宗的公案后,会茫然不解,不知其所以然,这是因为公案的道理是无法从相对的层次来理解的。记住:在绝对的层次永远不会有自我,所以公案的道理只有一点,也就是没有实体,没有自我。
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这两个层次的法,以一张桌子和椅子为例,对一般人而言是两件家具;而对物理学家来说,它们只是由能量所组成的粒子(particle)而已。物理学家下班后回到家,一样会坐在椅子上和使用桌子。
当佛陀说无一物,没有自我时,他是在说绝对层次的法,以绝对层次而言,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世界只是视觉和心理的幻象罢了。佛陀也说相对层次的法,所以佛陀也用「我」、「我的」、「你」等字,他教导与我们有关的事,如业(karma)、心清净、情绪、身心等。我们必须了解这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法,表达的语言因而大不相同。
当我们深入探讨这部经时,就会了解绝对层次的法,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佛陀告诉我们,一旦我们证悟绝对层次的法,必定可以永远解脱苦。佛陀所教的法和指导,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证悟-这是佛陀亲自证悟的经验。
现在的科学越来越能证明这些经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更妙:佛陀所说的法印证了今日的科学。绝大部份的科学家都未证悟,虽然他们知道:一切物质只是聚合又分散的粒子,却不了解他们也是粒子而已,没有实体;假如他们把自己也列入观察的对象中,这些科学家可能很久以前就已经证悟,而且很可能在教导世人如何证悟,而不是在教物理了。
我们也许听过或读过这些理论,也颇感兴趣,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实践,这些道理也就没有甚么用处。佛法最大的益处是它的可行性,而解脱道上的每一步都是切实可行的。
我所选的经典是《布咤婆楼经》,此经的副题是心识的各种境界(States of Consciousness)。在经中,佛陀对某人说法,并回答他的问题,所以许多佛经都是以人名为经名。此经是佛陀为布咤婆楼所说,故以布咤婆楼为经名。
大部份的佛经以「如是我闻」开始(巴利文是evam me suttam),原因是所有的佛经都是读诵的。第一次结集经典,是在佛陀入灭后的三个月举行,参加的全是阿罗汉,诵经的内容包括:说这部经的地点、有哪些人物在场,以及主要的问答等。这些内容使在场聆听的僧众能记住经中的场合,他们同意或不同意这部经的内容,如须更正,僧众可以建议修改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给孤独长者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他第一次听佛陀说法便皈依佛陀,成为佛弟子,那时由于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仍是游方僧,所以他想捐一座寺院给佛陀,他找到一座属于祇陀太子的芒果园,然而祇陀太子却拒绝出售,给孤独长者很有耐心,向祇陀太子请求了许多次,最后太子说,如果给孤独长者能以金币覆盖整座芒果园,他就会卖给他。给孤独长者命令他的仆佣们运来一箱箱的金币,想把整座芒果园覆盖住,金币用光了,还有一小片土地未铺上金币,最后太子也把这片土地供养佛陀,所以这座林园称为祇树给孤独园。
给孤独长者花了三分之一的财产买下这座芒果园,又花了三分之一的财产建造精舍。佛陀在此园中度过了二十五个雨安居。在印度,雨安居指在雨季的三个月,僧尼留在寺院学习和禅修,不外出托钵。雨安居的原因是:在佛陀时代,所有的僧尼都必须托钵,以获得他们的食物。在雨季,幼小的秧苗种在水中,隐藏在水中,僧尼不小心便把秧苗踩死,因此有农夫向佛陀投诉:僧众在雨季外出时,经常不慎践踏农作物。由于有上千位僧尼外出托钵,结果导致农作物欠收,使农夫挨饿,所以佛陀就规定僧众在雨季时,要在寺院安居,由信众把食物带到寺院供养僧众。雨季安居至今仍被遵守。
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与外道众三百人,住末利园中,提陀迦树(Tinduka)环繞之大讲堂。
在佛经中,称其他宗教的出家人为外道或苦行僧。末利(Mallika)夫人是波斯匿王(Pasenadi)的王后,她是佛陀虔诚的信徒,也是外道的施主。
尔时世尊,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然于其时,世尊念言:于舍卫城游行乞食,为时尚早,宁可往访末利园中提陀迦树环繞之大讲堂。
由于为时尚早,所以佛陀未去舍卫城(Savatthi)托钵。经中经常提到舍卫城,因为给孤独长者布施的林园就在舍卫城附近。虽然佛陀只在印度北部教化,但佛法却从此地弘扬到世界各地。
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与诸多侍众共坐一处,大声喧嚷,互相詈骂,耽于种种无益议论,即论王、论盗、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论饮、论衣、论床、论鬘、论香、论亲戚、论乘具、论部落、论村庄、论都市、论乡间、论妇女、论勇士、论市街、论琐事、论亡灵、论余诸杂事、论水陆起源,及论斯有斯无等。
经中一开始,一群以布咤婆楼为首的外道正在闲谈,谈论一些俗事及无益修行的话题。佛陀认为我们应该避免这些闲谈,因为谈论这些,不但会引起纷争,还会扰乱内心,会引起欲望、情欲等不善心所,也会产生执着和自我认同。即使今日,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井边仍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自来水,所以附近的居民在井边闲谈,并交换最新消息,这些闲谈经常会造成中伤、毁谤。这种闲谈是佛陀禁止的,因为这些言论无法产生智慧,也无法使我们的心转向修行、解脱。
尔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遥见世尊,自彼方来,即令其众,静默勿哗,曰:「诸君,肃静勿声。沙门瞿昙来矣。彼爱沈默,彼长老并赞叹沈默,若知吾等会众沈默,当觉此行不虚也。」彼等苦行外道,闻是言已,众皆沈默。
布咤婆楼看到佛陀走近时,以欢喜的心向佛陀问好,在下一段经文中,可以看出布咤婆楼是多么高兴能见到世尊。
布咤婆楼语世尊曰:「善来世尊,吾等欢迎世尊。世尊久未来此。请坐世尊。此座之设,为世尊也。」世尊就所设座而坐,布咤婆楼别取低座,坐于一旁。世尊告布咤婆楼曰:「布咤婆楼,汝等集此,以何因缘,为何论议?而汝等论议何故中止耶?」佛陀想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好帮他们解决疑难。
布咤婆楼闻是言已,答世尊曰:「世尊,吾等集此,所欲论者,可暂置之,因此等言论,世尊日后易得闻也。」布咤婆楼不想告诉佛陀他们在谈论甚么,因为他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问佛陀。
世尊,迩来颇有外道沙门、婆罗门,集此讲堂,就「增上想灭」发出议论,曰:「增上想灭,云何可至耶?」识(想)最究竟的灭尽境界(增上想灭),有时指第九禅(jhana)的境界,也称为灭受想定,在这个境界中,受和想(perception)的作用都会停止。我们将在稍后的篇章中讨论各种禅定。布咤婆罗所提的问题-灭尽,也是当时印度人认为是修行中最高、最究竟的境界,因此他们颇有兴趣。在巴利文,灭受想定为abhi-sabba-nirodha。Abi意为「最高」;sabba是「想」;nirodha是「灭」。整句或译为识(或想)的最高止灭(highest extinction),这是修行的极致。因此他们想知道更多有关灭尽定的境界。布咤婆罗继续说道:
或有人作是说言:想之生与灭,系无因无缘。当「想」生起,则人有知觉(conscious);当「想」停止,则没有知觉。此为彼等所说之增上想灭。
布咤婆罗听说灭尽定是指没有知觉,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灭尽定」不是指没有知觉,而是「想」和「受」的止息。布咤婆罗又说:
而余者作是说言:其实不然,「想」实人我也(是一个人的自我),它会生起和消失。当「想」生起,人便有知觉;当想(perceptions)消失,人便没有知觉。
布咤婆罗转述他人的见解,并使用「增上想灭」(识最究竟的灭尽境界)这个概念,其实他误解这个概念,佛陀稍后会向他解释。
复有余者作是说言:「不然,实有沙门婆罗门,具大神通与大威力,彼等于人,移想而来,掣想而去。移来则有想,掣去则无想。」此等人以如是说增上想灭。
复有余者作是说言:「实则不然,盖有天神,具大神力与大威力。其于人也,移想而来,掣想而去。移来则有想,掣去则无想。」此等人以如是说增上想灭。
印度自古以来便充满迷信,以上的观念便源于此。关于这个问题,佛陀认为:迷信和外力永远无法使人了解实相(truth),无法使人觉悟。布咤婆楼接着说:
世尊,尔时,我心生念言:「世尊精于此法。世尊熟知增上想灭。」请问世尊:何者是增上想灭?」读这篇文章,好像把我们带到古代的印度,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经中的人物,仿佛我们也在现场一般,我们熟知他们的习惯和所关心的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布咤婆楼是如何的尊敬佛陀。佛陀回答道:
布咤婆楼,彼沙门、婆罗门认为;「想」的生起和消失是无因无缘的,这种见解是错的。
佛陀对一些错误的见解,向来是直斥其非;而对于正确的见解,则一定会认同。佛陀接着说:
所以者何?有因有缘,人之想生;有因有缘,人之想灭。由于修习而一想生;由于修习而一想灭。云何修习?
佛陀此时尚未回答布咤婆楼的问题,因为「识的灭尽境界」是长期修行的结果,佛陀会从最初的修行说起。
布咤婆楼,今者,如来是应供、正等觉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者、天人师、佛、世尊。乃至身业语业,清净具足,具足戒行,诸根之门,悉为守护。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满足。
如来(Tathagata),Tatha意为「如」;gata指来或去;如来即是佛陀。上述的十个名号是形容佛陀的十个特质。
如来于此世间、天界、魔界、梵天界,于此大众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自身证悟,为彼等说法。
天界指天人住的地方。天人和天使相似,根据佛陀的说法,天人在福报享尽后,会重回人间,所以他们必须修行才能再回到天上。在每一节禅修前,我总会默请天人和我们一起禅修,那些想禅修的天人自然会来。天界众生的身体不像人类那么粗糙,所感受到的苦也非常少,所以不像我们有修行的意愿;而有些天人也乐于闻法,也会和我们一起禅修。
魔(Maras)即是撒旦,在这部经中,这个字是复数,应该译为心魔(tempter)。我们心中都有天使和魔鬼。梵天(Brahmas)是四禅天中最高的天界,他们不是创造者,不是造物主。
如来所说法,初善,中善,后亦善,文义具足,示教梵行,究竟清净,无与伦比。
佛陀所教的法中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文义具足」。要了解经文并不难,我们必须去阅读,并尽可能记住经中的内容。不只是学者,其他大众亦然,试着去找出经中最有趣的部分。而对想修行的人而言,这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去实践这些教法时,佛陀智慧的言语和精神才能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佛陀的意思,而他的教导才能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在这之前,我们只是知性上的认知罢了。
佛陀的教法(teaching)被称为法(Dhamma);佛陀没有教「佛教」,正如耶稣没有教「基督教」。佛陀想改革婆罗门教,而耶稣则想改革犹太教,虽然他们都失败了,却各自开创了新的宗教,并改革已失去原有精神,并衰退到只剩下一些仪式和仪轨的宗教;今天,在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问题。
佛陀接着说:
一个弟子因而出家,并受具足戒。
出家通常指成为比丘或比丘尼,并遵守出家人的戒律。出家人必须持戒,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法」的精神,可能会犯戒。对那些自愿遵守戒律的在家人而言,由于他们看到持戒的益处,内心的挣扎会比较少。
佛陀尚未回答布咤婆楼有关较高层次意识的问题。佛陀主张先持戒,以作为修行的基础。佛陀接着讨论五戒-五戒是所有戒律的基础。
今有比丘,舍杀离杀,不用刀杖,怀惭愧心,充满慈悲,利益一切生类有情,而住哀愍。
佛陀不只希望我们不杀生,还希望我们对一切众生慈悲,并由衷的关心众生的福祉。佛陀接着说第二条戒:
今有比丘,舍不与取,离不与取,取其所与,求其所与,毫无盗心,自住清净(过清净的生活)。
第一条戒可以对治嗔,第二条戒可以对治贪。在其他场合,佛陀建议以「布施」作为对治贪的方法,使我们放下「我」或「我的」等执着,并培养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慈悲等善念。
今有比丘,舍非梵行,净修梵行,行出离行,舍离淫欲,自住清净(过清净的生活)。
第三条戒是不邪淫戒,在此改为「独身」,即不淫。在比较严格的修行,不淫是最重要的戒律。出家人最重要的戒律即是不淫。如果破了此戒,比丘或比丘尼会被逐出僧团。有些在家人在三个月或六个月的禅修期间,也遵守不淫戒,这可以训练一个人的独立,也有助于克服强烈的感官欲望。
第四条戒占了较长的篇幅:
今有比丘,舍妄语,离妄语,说实语,正直诚心,不欺世人。舍两舌,离两舌。不会把在此处听到的话,到别处宣说,以免离间此众。也不会在此处重述「在他处所听到的话」,以免离间彼众。因此当有纷争时,他是个调解者;他鼓励人们爱好和平,使人们和睦相处,快乐的过生活,所以他只说促进和平的话。他避免说恶毒的话(不恶口),只说悦耳的话(和雅音),以及令人愉快的话。
他避免无谓的闲谈,只在最适当的时候说话,并说真实、重要、如法(Dhamma)和合乎戒律的话。他说的话被重视,因为都是合理的、合时宜的。他说的话与最终的目标有关。
「欺骗世人的人」是伪君子,说一套,做另一套。大部份的人都有直觉能力,知道我们所听到的究竟是来自说话者的亲身经历,抑或是道听涂说。「因此当有纷争时,他会是个调解者;他鼓励人们爱好和平…。」此处的重点是语言可以带来和平,我们可能读了上千本的书,而不为所动;而由衷的、真诚的的语言,关心人类福祉的话语,则能触动人心。
「他避免无谓的闲谈,只在最适当的时候说话,并说真实、重要的话。」在其他经典,佛陀教我们说话前要先思考,用词要精确,使人容易了解。「他说的话…与最终的目标有关。」这个目标是修行的最终目标-涅盘(Nibbana,梵文是Nirvana),Nibbana(涅盘)意指「不再燃烧」,也就是所有欲望的止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们可能不想放下所有的欲望。就世俗人而言,这种心态当然没有问题,然而要知道,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证入涅盘-要止息所有的痛苦烦恼。
当佛陀说:我们应该说一些有益的、能激励人心的话,谈论「法」(Dhamma)时,应该正确的表达,并掌握重点。这种「法谈」可以使我们解脱苦-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问题是我们如何达到这目标,我们必须找出「我不想放下我的欲望」和「我想去除所有的苦」之间的关联。透过观察苦如何生起的,我们可以在观察时自问:「我甚么时候开始受苦?」,「苦何时生起?」,「为甚么我会受这种苦?」每个答案都会引起新的问题。假如你深信自己没有苦,那么可以自问:为甚么我想要禅修。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因为它会使我们去思考是否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苦,并使我们去找出苦因,并永远去除这些苦。
第五戒是不饮酒和不吸食麻醉物品,这部经没有提到这条戒,取而代之的是对弟子们的告诫:「不可损坏种子和农作物。」在某些佛教国家,由于社会环境使然,这条戒被误解为出家人不可以在园子里工作;事实上,是指不要损坏农作物,而不是不可以照顾和种植花木。因为佛陀在经中教导苦行外道,这些外道是修行人,他们想知道有关修行的更高层次,而他们视「受持不饮酒和不吸食麻醉药品戒」为理所当然,所以佛陀省去这条戒律。
佛陀接着说「不非时食」戒,这是沙弥和沙弥尼应该遵守的,而参加密集禅修的在家人也会受持这条戒。对我们来说,可能指不随意打开冰箱,或是身上不带巧克力,以免随时想吃它几口。这条戒律是希望我们在饮食上能节制;如果我们想要更严格的自我训练,可以每天只吃一餐,或在某个时段禁食。
「他不观看歌舞表演」,因为娱乐会使人分心,甚至会引起情欲,这些与贪欲或希望满足感官之娱有关。如果我们想精进禅修,为了让心保持平静,最好能避免这些娱乐。
「他不着花鬘,不涂抹香水,不事装饰」。世人无不想使自己的外表更迷人,这会使我们对自我产生执着。如果我们很富有,我们会用贵重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来突显自我的价值感,认为:「如果我拥有贵重的东西,我就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想法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却是一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不接受金银」指出家人不可做商业买卖,要过简单、俭朴的生活,不追求世间利益。经文接着列出哪些是适当的供僧物件,也列出了哪些是不适当的,如:生米、生肉、女人、少女、男佣、女佣、羊、鸡、猪、象、牛、马、田等。因为这些东西会引诱僧众去过世俗的生活,而忘记修行。
不为使者(替人跑腿),不为中介,不事商贾,不以秤升或尺,欺诳世人。不得贿赂谲诈…有趣的是,起初佛陀度化弟子出家时并没有制戒,他只简单的说:「善来,比丘。」想出家的人便可追随佛陀过出家的生活。后来出家的人越来越多,僧众良莠不齐,有些僧众禁不起诱惑,佛陀因此制定一些行为规范,让僧众遵守,并沿用至令。
欺骗和不老实是未证悟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或许有人不同意以上所说的戒律,然而只要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就可以改掉一些坏习惯,而这些坏习气是不利于修行的。稍后佛陀会回答布咤婆楼的问题。通常佛陀说法是先从日常生活的持戒开始,接着一步步的说到禅修,最后引导我们证入究竟实相。
第二章
守护根门:正念与正知
佛陀向布咤婆楼说明修行的起点-持戒后,接着说:
…布咤婆楼,比丘如是具足戒行,依戒而行,故无论身在何处,皆无怖畏。
要使事情完美必须经过训练,智者不会把这种训练视为强迫的,而会视为可以培养自制力,因为透过降服自己负面的本能(instincts)和冲动,我们会看破一切产生痛苦的假像。佛陀教的每一种法都在引领我们更接近这个目标。显然的,「无论身在何处,皆无怖畏」会带来安全感。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过错,便不会失职或有罪恶感,因此会感到轻松自在。佛陀举了一个譬喻:
犹如已灌顶的剎帝利王,已降伏所有敌人,故无论身在何处,皆无怖畏。比丘亦复如是,由于具足戒行,故无论身在何处,皆无怖畏。由于受持圣(Ariyan)戒,比丘有无咎之乐。
乐(bliss)指内在的喜悦,这不是禅修所产生的喜乐,而是知道自己无可责备,不再受欲望折磨之苦,因而产生的满足感。Ariyan是圣洁的意思,受持圣戒比受持五戒需要更高程度的出离。例如,五戒中的第三戒是不邪淫,而出家人则要求禁欲(不淫)或独身。
佛陀继续讨论下一步的修持-守护诸根。佛陀仍然不想回答布咤婆罗有关「识的灭尽」的问题,因为布咤婆罗仍无法了解正确的答案。
今有比丘,眼见可见物(外境)时,不执取总相(major signs),亦不执取别相(secondary signs)。如果他不守护眼根,贪爱、忧伤、不善心境将充满其心。所以他守护眼根,使眼根受到节制。
佛陀接着叙述其他五根,经文如下:
今有比丘,以耳听见声音时…;以鼻闻香时…;以舌尝味时…;以身体接触外物时…;以意(mind)思考时…不执取总相,亦不执取别相。如果他不守护诸根,贪爱、忧悲、不善心境将充满其心;因此他守护诸根,使六根受到节制。
佛陀接着说:
比丘由于受持圣戒,守护诸根,故有无咎之乐,比丘如是守护诸根。
这几句开示经常被人误解为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尝、不要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了感官,就必须看、听、尝、碰、闻;禅修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心不可能不去想。
当然不去看某样东西便不会受它干扰,然而我们如何能不看东西呢?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持戒的话,正确理解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不执取总相,亦不执取别相」是甚么意思?眼睛只看到颜色和形状,其余的都发生在心里,以看到一块巧克力为例:眼睛只看到一块褐色的东西,是心在说:「啊!巧克力,一定很好吃,我想要一块。」「不执取总相,亦不执取别相」是要制止这种念头的生起。
这方法用在我们非常喜欢或非常讨厌的事物上,特别有效。人最敏感的两个感官是视觉和听觉,我们可以选其中一个来修,观察心有甚么反应,并看看心如何编造故事(storytelling)。其实眼睛和耳朵并没有选择看甚么和听甚么的自由,例如,耳朵听到了货车经过的声音,心会立即反应:「货车」,接着会反应:「真吵,吵死人了,怪不得我无法禅修。」后来发生的全是心的造作,和声音没有关系。声音只是声音,颜色只是颜色,而形状只是形状。
有时候,受持不淫戒的人会被告诫不要看异性,这怎么可能?我曾遇到一些如此修行的比丘,最后造成不自然、尴尬的人际关系。你怎么可能和一个故意不看你的人说话?这绝不是守护根门的意思,而是当眼睛看到形体时,心中标明(labeling)如「男」、「女」,便停在那里,不要让心再想下去,因为如果心再想下去,可能会生起贪或嗔,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大多数人都能修持这个法门,一旦照着去做,生活会轻松多了。以上街购物为例,上街前,我们拟了一张购物单,都是真正需要的,然而当眼睛看到一堆堆包装精美、大特价的商品,心马上被吸引,最后我们买的要比实际需要的多。有些人逛街只是为了找一些吸引他们的东西;如果有钱的话,有些人把购物当成一种消遣,当成周末的节目。
如果我们很容易受外境影响,最好的方法是去观察感官接触外物的那一刻,并使「想」蕴不在心中生起-即不再标明事物。在此之前,要停止心的作用是很难的。例如,如果我们看到或想到某人,不论喜欢或怨恨他,或看到我们既不讨厌也不喜欢的人,我们应该将心停在「标明」的那一刻,也就是知道对方是个人、是朋友、是男是女等,仅此而已,其余的部份都是我们的欲望,这是守护根门的意思。
感官用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能看、能听当然比失明、失聪容易生存,而大多数人认为感官的存在是为了带来快感,我们就是这样使用感官,一旦感官无法带来快感,我们便会生气,会迁怒他人。如果某人惹我们生气,我们就会责怪那个人,其实跟那个人根本无关,那个人和我们一样,也由地、水、火、风等四大组成,有相同的感官、四肢,也和我们一样追求快乐,那个人根本没有使我们生气,是我们的心在生气。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在使我们快乐的人身上,他(她)和我们一样也由四大组成,有同样的感官,同样的四肢,也同样追求快乐,根本没有理由去要求那个人使我们快乐,或在那个人不能为我们带来快乐时责怪他,我们只需看清一点:他是一个人,仅此而已,别无其他。在这个世界上有芸芸众生,为甚么要让这个人来决定我们的苦与乐呢?
我们能把根门守护好,便能防止欲望的生起,这样我们便能更有舍心(equanimity)的过生活,而心也不会像跷跷板一般,起伏不定,当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心便往上扬;当得不到时,心便如跷跷板般往下落。在这个世间,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环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永远满足;世间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感官接触而已:看、听、尝、触、闻和想,这些都是短暂的,必须一再的追求,而追求感官欲望会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事实上,不是感官接触为我们带来满足感,而是心生起满足感。
如果我们想要平静、和谐的过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守护根门,这样便不会因为想要所没有的东西,或想推掉已有的东西而烦恼,这是两个苦的因。只要我们能守护根门,不让心超过标明的阶段,那么我们便能够轻松自在的过日子。
心像极了魔术师,心能随时变化,只要一越过想蕴(标明)的阶段,心就开始变戏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贪和嗔很快就会生起。佛陀曾提到魔罗(Mara),即心魔(tempter)。魔罗经常和我们一起,并伺机入侵,其实诱惑是可以避免的,当诱惑出现时,我们必须去克服,我们可以在诱惑未生起前,便阻止它的生起,这是守护根门的意思。
佛陀在教导布咤婆楼有关「较高层次的识的灭尽」和禅修的方法前,仍有许多话要先告诉他。佛陀接着提到正念和正知。这种说法的次序也出现在其他经典:首先是持戒,其次是守护根门,接着是正念、正知,后两者经常被放在一起。正念的巴利文是Sati,而正知则是Sampajabba(或译为正智)。
比丘如何具足正念正知?今有比丘,若进若退,正知之;瞻前后视时,正知之;若屈伸手足,执持衣钵;若饮食嚼尝,若大小便利,若行住坐卧,若眠寤语默,皆正知之;于一切时,皆正知之,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知。
正念有四个层面:即对身、受、心、法(想的内容)保持正念。身念住是其中最重要的部份,不只在禅修期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在禅修以外的时间不能保持正念,那么在禅修期间也不能,所以必须时时保持正念,因此我们以「观察我们的身体」作为第一个念处(身念处)。我们要觉知所有的动作;无论行住坐卧、穿衣、卸衣、屈伸手足,都要观察。修习身念处最大的益处是能把心放在所缘境上,不会让心到处乱跑。
修习身念处的第二个好处是能净化内心。当我们在观察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时,烦恼、忿怒或贪心就无法生起。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要把身体当成正念观察的对象。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感受身体,可以碰碰身体。修身念处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无须去找念处(观察)的对象。如果我们能持续修习身念处,在短时间内,心就会平静下来,心中不再波涛汹涌,因为当心在观察身体的动作时,忿怒、贪欲、厌恶等恶心所就无法生起。
第三,正念可以让我们的心安住在当下。最后,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过去和未来。通常我们会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只有当下才是真的,而过去和未来都是心所创造的,它们来自回忆和想象。许多人活在过去和未来,或活在过去与未来两者当中,果真如此,那么要保持正念和禅修会非常困难,因为正念和禅修只能在当下为之。
觉知我们的情绪和感受是第二个念处-受念处;第四个念处是法念处。我们将立刻讨论第三个念处-心念处。在禅修时,法念处和受念处都是观察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须修习这两个念处。例如有强烈的情绪生起时,首先,我们要觉知它的生起,然后以善心来取代不善心,我们没有必要受情绪影响。如果去追溯各种情绪是如何生起的,我们必能发现它来自感官接触,这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观察我们的念头,如果我们知道某些念头是善的,我们只是观察它,等它消失后,我们再以正念观察身体的每个动作;如果是不善心,我们尽快以善心来取代。不善心停留在心中的时间越短,发展成负面心态的机会也越少。我们越能觉知我们的贪心和嗔心,便越不会让贪与嗔在心中生起,也越容易从贪与嗔的烦恼中解脱。
第三个念处是心念处,心也是很重要的观察对象。如果我们能在不善心发展成思考或情绪前便觉知到,那么,取代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有些人的心念经常是负面的,并且很难改变这种情况,大部份的人都在正面和负面的心境中摇摆,也有人的心大部份时间是正面的。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心境是负面的,心中的怨恨、妒忌和厌恶会引起负面的想法和情绪,那么我们要避免这种恶心所的生起,并知道这些只是一时的心境而已,而我们所有的、所想的或所作所为,都是无关紧要的。一旦发现这些心境会使我们不快乐,就无需保留;我们越快乐,就愈能和身边的人分享。如果自己都不快乐,如何能与他人分享快乐?我们不可能给人一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至于为甚么有些人自称可以,这是一个谜。
四念处是指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和法念处。正念意指纯然的觉知,其中没有些微的判断。下判断是正知(clear comprehension)的作用,以正知来判断感受、情绪、心境和思想内容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以便有需要时可以取代。我们都有正知-有明辨的能力,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当然我们也有一切人类都有的小缺点,也就是那些不悦、忧虑、掉举(restless)、烦乱的习气,然而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些缺点,有了正知,我们便能观察这些缺点,并以善法来替代这些不善法。我们在禅修时观察这些心念,并学着放下这些不好的心念,继续观察禅修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修行。
人为甚么放不下消极的心态?唯一的理由是他们为自己辩护,给自己找理由去责怪他人或外在环境,这样无法带来快乐。在修行之旅中,我们必须如实的观察自己,而不是希望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或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
坦然面对自己会带来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解脱的感觉,仿佛放下了重担。只要保持正念,心会从散乱的思绪和反应中解脱。不断对外在环境作出反应,会消耗许多心力,因为这些反应往往是吹毛求疵和带有批判性的,有了正念便不会发生这些情况。
无论是按照字面意思或就比喻来说,正念指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专注在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上。当然,有时我们会失念,每当我们发现了,便再提起正念,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事。
正知有四个层面,《布咤婆楼经》没有提到。第一是要觉知到我们想做或想说的是甚么,并去观察它的目的是否有益,如果是自我中心或只顾自己,这是无益的。一旦了知我们想说或想做的是有益的,就进入第二层面:要确定我们是否有适当的方法去达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第三个层面是:自问:该目的和方法是否如法,以另一个方式是去问是「佛陀是否同意?」我们根据所了解的佛法来自我检查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最重要的是看看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戒律,有没有慈悲心?能否带来幸福?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行为能否使我们达到灭苦的目标?思考这些问题后,我们便不容易走向歧途。
世间有森罗万象的事物,除非我们有凡事思考的习惯,否则很难避免造恶业,假如前三个层面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付诸行动了。第四个层面(步骤)是:已经作了(说了)我们想做(想说)的事后,去观察看我们是否真的达成目标,如果没有,那么要想想看有甚么缺失。
以上是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最有益的方式」来解释正知。首先,我们必须以正念来觉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现象;接着,以正知来检视我们的意图,如此修习,我们的本能反应自然会慢下来,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冲动容易犯错,谨慎反而使我们走向正途。接下来,佛陀讨论有关生活必需品的满足。
比丘如何自知满足?今有比丘,以袈裟护身,自知满足;以钵食养身,自知满足,并在获得足够供养后离去。如有翼鸟,任飞何处,只有羽翼随身。比丘如是自知满足。
在今日的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比所需要的多。佛陀说只有四资具-饮食、蔽身之所、衣服和医药是必要的。而大部份的人所拥有的东西远远超过这四种资具,虽然有些是必要的,而其他的是不必要的。去检视一下我们是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还是出于贪欲,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然后,再问问自己:「我对所拥有的东西是否满足?我是否了解知足的可贵?我知道大部份的人都不了解知足的可贵吗?」我们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医药,又没有片瓦遮顶吗?想想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的人,是否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呢?通常,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赏心悦目,或尝到不合口味的食物,或碰到我们不习惯的事,我们往往会抱怨,而不会感激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发现:去抱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感恩拥有这些东西要容易多了。
佛陀曾经和弟子们在海边漫步。佛陀对他们说:「诸比丘,若有一盲龟游于海中,而此海龟每一百年才浮出海面呼吸一次,而海中飘浮着一根木轭。诸比丘,你们认为这只盲龟的头能够穿过这根木轭,浮到水面上吗?」,「世尊,这是不可能的。」佛陀说:「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大可能。」佛陀接着说:「能转世为人,而又诸根完备、四肢健全,又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也是如此稀有难得。」我们可记得这些教诲,以培养知足的心?在禅修时知足是非常重要的,心愈不知足,就愈难禅修,因为不知足会使心烦乱。由于我们认为自己的禅修并不是很顺利,所以会不满足;或是想到达某种境界,或是想证悟;任何一种不能满足的想望(wanting)都会使内心混乱,使情况变得更糟。除非我们有知足的心,否则禅修会徒劳无功,我们的禅修会愈来愈差,而心也会愈来愈不知足。任何事情,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一定可以做好。如果我们总是不知足,不知足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心里会想:「我非常不满,因为…」然后我们会为自己找许多理由,这些理由大都是很愚蠢的,与衣服、饮食、住所、医药无关。
我们应当记得佛陀说过「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拥有所有维生的必需品,因此我们可以继续修行,当我们充满感恩,感谢良好的环境,感谢有那么殊胜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禅修。不满足的心会到处乱跑,想找到使自己满足的事物。禅修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首先,我们应该培养知足的态度,并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四种必需品又称为四资具(Four Requisites)。在现代社会,为了谋生和沟通所需,我们可能需要许多东西,而有些东西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没有这些东西,也一样可以生存。有一种观想(contemplate)很有帮助,也就是花点时间来观想所拥有的一切,并心存感恩,而不去贪求其他事物。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不足之处,如果我们观想这不足之处,那么不满足的心便会生起,并耿耿于怀。相反地,如果我们只想一些使我们心满意足的事,那么,满足的心自然会生起。这个道理很简单:每当我们将心放在某处,只觉知到该处所发生的现象。我们不要有一些负面的想法,然而偏偏经常如此,这是人们的毛病。我们习惯把心放在使自己不愉快的事上,即使知道这样做会使我们受苦,我们仍然明知故犯。或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负面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愈了解自己内心的人,愈容易放下一些没有帮助、又不能带来平静和满足的事物。
知足者有非常轻松的感觉,因为放下了总是期待景况与人事变动的重担。事物会如实呈现,如果不愿接受这些事实,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烦恼;这就像在推一扇锁住的门一样,我们一再的推,直到推得手痛,仍然无法把门打开,如果我们够聪明,就会接受这个事实,门锁了就锁了,没有甚么大不了的。
我们应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生命,一切事物本来如此,我们只能如实的接受。所有事情都以应该发生的方式发生,都各有自己的因和果,即使我们平日无法看清楚,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把生命中所遇到的逆境当成一个个学习的机会。如果碰到不如意的事,把它当成学习的好机会,不要逃避,也不要期望它有所改变,因为这样必定会使自己痛苦。我们要自问:「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是极大的损失。
生活犹如一所成人教育学校。如果我们如此看待生命,我们会正确的观察生命现象。如果我们希望生命充满乐事,那么我们必定会失望,除非我们了解到:我们来这个世界是要学习的(we are here to learn)。在这所成人教育学校,有各种不同的课程,我们被编入最适合某种课程的班级,这与年龄无关,而与我们内心的成长有关。每个人都要面对所需要学习的事,如果我们无法从中学习,无法通过考试,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班级,再学习同一门课程。直到我们的内心成长到足以通过考试,才能继续修下一门课程。
布咤婆楼和我们一样有许多课程要学习-持戒、守护诸根,以及培养正念正知,这些课程都有助于达到「识的最高灭尽」,而布咤婆罗在他的修行之旅中,必须了解和修习这些课程,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第三章
终止五盖的作用
(比丘)具足圣戒聚,制御诸根,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满足,离世闲居,或在静处,或在树下,或在山谷,或在岩窟,或在坟冢间,或在林薮,或在露野地,或在藁堆。比丘乞食而还,食后,结跏趺座,端身安坐,正念现前。
在这段经文中,佛陀开始讨论禅修,我们知道不是把腿盘起来就是禅修,还要使「正念现前」。
在修习安般念(anapana-sati,数息观)前,在观察出入息能带来任何重大改变前,我们必须先从佛陀所说的五盖(hindrances)中解脱出来。
珨﹜贪欲盖
(比丘)弃除贪欲,住于无贪欲心,离去贪欲,使心净化。
这个盖(hindrance)经常被称为「贪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如果我们被任何欲望所缠缚,很明显的就无法禅修,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把欲望放下。经常困扰行者的贪欲有:「天气太冷,太热,膝盖很痛,我的背部很不舒服,我好饿,我吃了太多东西,我想喝水,我觉得不舒服,我需要睡个觉。」在心中生起任何类似的念头都会使禅修中止。
所有来自外在世界的事物必须透过感官进入我们的心,而禅修的体验则无须依靠外境。一旦我们有入定的喜乐,便会发现由禅定所生的喜乐能对治贪欲。如果心能达到一境性(one-pointed),贪欲就无法生起。我们越能达到心一境性,心中便越少挣扎;不会为了食物、舒适、温暖或其他我们想要或不想要的东西而挣扎。所有的苦都来自贪欲;贪欲越多,痛苦烦恼也越多,连「我想有一节很好的禅修」也是贪欲。
贪欲与错误的信念(belief)有关,也就是误认为快乐来自感官接触。我们当然有许多快乐的时刻,当我们不断的向外追求感官接触,认为它们会带来满足,就会封锁我们通往禅定、清净和离苦之路。只要我们沉溺在欲望中,就会受苦,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必须放下贪欲。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了解,加上坚定的意志才做得到。
一种捕捉猴子的陷阱最能说明这点。印度的猎人设计了一种用树枝做的猴子陷阱,它是漏斗型的,开口很小而底座很大。猎人在底座放了甜点,猴子要拿这甜点,就要把爪子伸进很窄的漏斗通道,当猴子拿到了甜点后,无法把爪子抽出窄窄的通道,由于猴子通常不愿意放下甜点,于是成了猎物,猴子只要张开手掌,便可以轻易逃出陷阱。我们也一样,很难放下心中的欲望。
一旦知道苦如何生起,就不会受喜欢或不喜欢的念头的影响,我们才会有好的修行,才能了解「放下欲望便能止息妄念」。一旦我们依此修行,马上就会看到成效,然而要小心不要急于求成,因为急于求成的欲望本身就是苦,这是世俗的欲望。「我想要…,我非常想…」,所有类似的欲望都应该舍弃。解脱道上没有甚么值得贪求,只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们要了解哪些是必须做的,目前手边有甚么工作要做,然后去做,仅此而已。
佛陀为五盖作了比喻。贪欲如负债一般,我们欠了感官接触的债,于是不停的还,又不断的举债。除非我们了解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就像不断举债,并成为我们唯一关心的事。一旦得不到所想要的,或是它不持久,我们就会不快乐,甚至会抱怨某事或某人。追求感官的满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保留感官所接触的东西,无论是景物、声音、气味、味道或念头,都是生灭不已的,这种满足要依靠外境产生,而在生灭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在譬喻里,负债的人总想还债,意指我们经常要为追求愉快的感官接触而忧心。一旦我们了解这种追求是没有必要的,这就像还清债物一样,我们不再欠感官的债,无债一身轻。正如佛陀所说的,这才是值得高兴的事。知道我们不再追求感官欲望,这种觉悟会带来很大的安全感和独立感;相反的,如果我们放不下心中的贪欲,我们便会经常烦躁不安。
二、瞋恚
(比丘)弃除害心,弃除瞋恚,住不害心,普为利益慈愍一切生类有情,离去害心与瞋恚,使心净化。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打坐时,瞋心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在每一次的禅修前,我们应该先对自己,然后再对一切众生散发慈心。有些人发现很难去爱自己,因为喜欢自我批判和讨厌自己。果真如此,这种人会很难去除贪欲,因为他们认为感官欲望满足了,便能产生自我满足感。他们有接受自我(self-acceptance)和怜悯自我(self-compassion)的心态,然而世上没有可以永远满足的欲望,因此我们必须一再的追求,以满足欲望,这样只会带来更多的苦。我们必须学习对自己散发慈心,尽管我们有许多缺点,一个爱自己的人,才能不挑剔、不批判的爱其他人。
对慈悲心而言,完美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世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事物,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世事与世人应该是完美的」这种想法是多余的,这种观念会造成紧张和压迫感,因为这种想法会产生欲望。放下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以及放下欲望,我们会感到轻松和解脱。
假如我们很难对自己散发慈心,那么可以修习两种特别能生起慈心的方法。首先,观想我们最爱的人,并对他散发慈心,然后再把慈心散发给自己,其中不可有任何欲念,否则这个方法会无效。散发慈心时,只有关怀、包容、想要帮助他和有祸福与共的感觉。第二个方法是回忆我们以前所作的善业。透过回忆,将过去的善业带回当下,重新回味那些善行,觉得自己也是不错的,此时,让我们去爱那个以善心去做好事的自己。将慈心散发给自己后,我们应该想到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他们也追求安宁和快乐,但只有少数的众生可以如愿以偿,我们也把慈心散发给他们。
如果我们把对周遭的人或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的敌意留在心中,我们就必须记得:越能放下瞋心和恶意,越容易禅修。佛陀说:当心中充满瞋恨时,是不可能禅修的;而有慈悲心就可以禅修了,慈悲心是我们给自己的礼物。在禅修时,我们必须全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投入禅修,没有任何的「我」留下来,或是有另一个「我」想解决某个特别问题,想找一些方法来满足某种欲望,虽然我已看到佛陀所说的法(truth)。
佛陀在一篇开示中,以替国王打仗的战象作比喻。如果战象只用脚来为国王打仗,那么它不算忠心;如果只用头打仗,而保护身体其他部位,也不算忠心;同样的,如果只用象鼻,而保护其他部位,也不算忠心。只有在上阵时,这只战象用全身的每一个部位,全心全力为国王服务时,才是忠心的。我们在禅修时经常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会有所保留,我们会想:「我可以获得甚么好处?这是正确的教法吗?怎样才可以使禅修按照我的方式进行下去?当我的这个或那个欲望满足后,我的苦一定会消失。」所有这些想法都会使我们有所保留,无法全心投入禅修。当心不散乱,达到住心一境时,此时,贪欲就无法生起,因为心完全专注(不会分心),不再有观察者,只有经历者〈experiencer〉,因为心已经和所缘境合而为一了。此时已进入完全的定。
佛陀将恶意和嗔恨比喻为身体的病苦。大家都知道生气的感觉-热、烦躁,非常难过,这些只是轻微的症状。这是为什么有人说:那些瞋心重的行者是最好的禅修者,因为总是感到不舒服,这使他们有很大的动力去修行。佛陀曾拿瞋心和胆疾比较-胆汁(坏脾气)不断在心中生起。
瞋心是三不善根之一,另外还有贪和痴。我们也有三种善根:慈爱、慷慨及智慧。我们可以全权选择要加强哪些根。痴(delusion)意指错误的观念,亦即认为有个实体称为「我」,并且必须保护、支持、照顾这个「我」,而且要不断满足我的所有欲求。由于「痴」,当想要某些东西时,「贪」会生起;当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嗔」会生起。我们无法直接对治「痴」,因为贪和瞋太强了,障蔽了我们的智慧,一定要先对贪和瞋这两个敌人下工夫,试着减弱他们的根。
禅修时,我们要去除瞋心。假如有特别不喜欢的人或事,在禅修前,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将在下一节的禅修中,让所有的不悦离去。」这一节禅修后,如果我们想继续生气的话,没有人会阻止我们。如果我们的嗔怒连片刻都无法停止,就无法禅修。去除瞋心,就像从大病中康复一样。
三、昏沉及睡眠
(比丘)弃除昏沉,弃除睡眠,系想光明,正念正知,离去昏睡,使心净化。
在禅修时,我们经常为昏沉及睡眠所困扰,这是第三盖-昏沉及睡眠的例子,克服的方法是「系想光明」(perceive light)。系想光明有两个方法,如果真的昏昏欲睡,在入睡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张开眼睛,望向光明处,直到我们醒觉,然后再闭上眼睛,在心中系想光明。一般情况下,「系想光明」能去除因缺乏动力和正精进所引起的昏沉及睡眠。正精进不是身心的紧绷和僵硬,而是觉醒与觉知(awareness)。
当禅修的心变得昏昏欲睡时,就无法觉知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就如踩在上了蜡的地板一样,任意向四处滑动;心既无法觉知任何念头,也无法观察禅修的对象,这就是昏沉与睡眠,这时候我们应该暂时停止禅修。由于禅修使人心情颇为愉快,所以许多人会继续禅修下去。
当心处在一种非醒非睡的状态时,我们很难觉察到苦,我们要立刻舍离这种状态,因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应该睁开眼睛,并移动身体,让血液流通,或拉拉耳垂,或揉揉脸颊;为了克服昏睡,最后可以站起来。我们也可以鼓励自己:「现在是禅修的时候,希望我能禅修得最好(make the best of it)。」这不是希望能从中得到什么,而是尽力而为。
如果「系想光明」是自然而然的话,通常这是已进入禅定的征兆。每当发现心不专注时,也可以刻意系想光明,这时候的心或许已失去动力,或是从来都没有修行的动力;或是忘了禅修的目的。如果能系想光明,则能照亮心中黑暗的角落,这是五盖的躲藏处。
佛陀将昏沉与睡眠比喻为坐牢,当昏昏欲睡时,我们便无法动弹,虽然我们有锁匙,却无法使用。我们必须有禅悦和精进,当有了禅悦和精进时,心会受到鼓舞;有一颗鼓舞的心,我们就可以禅修了。佛陀也说过:多了解一些法(Dhamma),对修行会有所裨益。
四、掉举与恶作
(比丘)弃除掉举,以及恶作,使心轻安,内心寂静,去除掉举,以及恶作,使心净化。
我们要了解「内心寂静」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希望禅修能使内心平静,而佛陀却说:内心要先平静才可以禅修。当内心烦躁不安时,我们更要记住佛陀的话。我们要找出烦躁的原因:「为甚么我的心不平静?是什么欲望在扰乱我的心?为甚么我会这么不安?」如果心不能安止在一处,那么身体也不能。掉举(reatlessness)在我们无法获得想要的东西时生起,所以应该观察这个烦扰(agitation),仔细的找出这个欲望,并问自己:这个欲望满足后,心是否真的会平静下来?我们何不直接放下这个欲望,同时也放下了这个欲望所引起的苦和掉举,使内心平静。
在这段经文中,佛陀说到:「内心寂静,使心净化…」内心不但不再烦躁不安,由于欲望不再生起,心也得以净化。这时心很轻松,有平静的心(even-mindedness),感到自己和周遭打成一片,不再担忧所缺乏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缺少甚么,我们拥有一切所需的;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蒙闭了我们,所以无法看到真相;如果我们能够舍弃这些想法,禅修便容易多了。有一种想法是心需要靠外境才能平静下来;事实上,平静本在心中,只要放下对外境的执取,便可以使内心平静,这取决于我们的心念。掉举与恶作永远和欲望有关,一旦觉察到这一点,便要立刻放下欲望,这样内心才能净化和平静下来。
「担忧」通常与未来有关,我们希望未来的事按照我们所计划的方式发生,这种生活方式是荒谬的,因为太在意未来发生的事,会错失当下,而当下才是我们所拥有的时刻,也是最重要的一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掉举」在心向外寻求满足时生起。一旦了解我们已经具足一切所需,或许更容易放下心中的不安(unrest)。
许多人有做不完的事,有趣的是所有的事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即使事后有所抱怨,我们所做的都是自己选择的。忙于各种活动使人觉得自己很重要,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somebody)。掉举为日常生活带来许多难题,因为掉举会使人陷入不同的处境,而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处理,最后感到事情多到难以应付。我们应该知道掉举是五盖之一,是一种障碍。
佛陀把掉举和恶作视为奴隶状态,我们被情绪摆布,让它成为我们的主人,让恶作、忧虑充满内心,以致无法独立思考。禅修者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不是指要去发明一套新的修行方法,以及独自完成每一件事,没有必要。我们非常幸运,因为佛陀的指导是垂手可得的。而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脑袋,能将佛法中不同而相关的部份连接起来,并且知道如何互相配合-起初看起来像一幅大拼图,由许多图片所组成,渐渐的我们知道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并能够看到整幅图画之美。
五、疑
(比丘)弃除疑惑,心离疑惑,于善法无有疑惑,离去疑惑,使心净化。
为了去除疑惑,我们要能分辨善恶,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事情有助于我们达到解脱的目标。而在这部经中所提到的目标是要培养一颗平静的心,我们需要一颗平静的心来禅修。疑会使我们错过轻安(tranquility)的经验,我们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禅修,以及担心禅修太难,或许我们也会怀疑禅修指导,怀疑是否应该遵守禅修指导。事实上,长久以来的经验证明,遵守禅修指导的禅修者都有很好的成果。这些指导来自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传统,是非常可信和可靠的,这些禅修指导不断的被实践;而我们对修行的见解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这种个人的见解往往受到自我形象和外在环境的限制,既不可靠也不可信。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接受佛陀的教导,并依教奉行,那么,我们就不会心生疑惑。我们的心非常喜欢幻想(conjure up)各种的概念和可能性,有时或许能证明佛陀是错的,这是非常好的消遣,尤其是当禅修不太顺利时:「这套修行方法一定有不妥之处,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所以一定不是我的错,或许佛陀并不是甚么都知道的。」疑,仿佛是个狡诈的敌人,我们会怀疑佛、法、僧和导师,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禅修指导,甚至整套教法。这些「疑」不但使我们难以禅修,甚至使我们无法修行,因为心忙着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如果真的想禅修的话,一定要放下所有类似的想法。
我们也要放弃追求完美的理想,因为追求完美是一种执着;事实上,我们必须放下所有的观念,只管修行。「疑」使我们很难全心投入去走修行之路,如果没有修行的动机,修行道上会充满荆棘。「疑」也使我们在各种教法(teaching)中游移不定,使我们无法投入任何修行中。我们一再尝试新的方法,又半途而废。全心投入指完全付出。要做到这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佛陀说:「疑」犹如在沙漠中旅游,身边只有少量的食物,又没有地图,在漫长的旅途中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确定甚么是有利的和应该走哪条路,这种犹豫经常妨碍我们的修行。虽然我们知道:透过修行,我们的了解会更深入。禅修使我们的心变得能适应、有弹性、更柔软,也因此能知道更多。
疑和审察(investigation)不要混淆不清。去找出自己与所接授的方法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有甚么影响?我要如何修才能了解实相?」另外,「疑」不是信(belief)的相反,佛陀从不赞成盲目的信仰,而是希望我们对他所说的,能培养足够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没有疑惑下修行。
在另一部经典中,佛陀谈到禅修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要知道自己的苦,知道苦从何而来,如何困扰我们。其次是从教法(teaching)中得到信心,知道自己也可以走这条修行的路。第三是为自己有机会能修行而感到喜乐。只有当这三个因素都具足时,禅修才会有成果。这里所说的喜乐,并不是世人所谓的高兴,例如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感激、高兴;又如看到美丽的景色后,所感到的快乐等。而内在的喜悦(inner joy)是当我们找到究竟解脱的教法,以及我们正逐步迈向这个目标后产生,这非常有助于禅修。打坐时,如果我们在想:「唉!又要再坐一支香,我想我一定要撑到底。」这样我们永远无法好好禅修。禅修时,必须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和振奋的心;虽然禅修能强化两者,而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有这种力量和心态。
每个人都有五盖,而每个人都会发现某种盖为我们带来较多的麻烦,所以去找出哪个盖是自己的敌人,是非常值得的。如果是「昏沉及睡眠」盖,那么就要系想光明;如果是「瞋恚」盖,就去修慈心禅;如果是「贪欲」盖,就要去想欲望给我们带来的苦,并放下这些欲望;如果是「掉举和恶作」盖,我们知道这和欲望得不到满足有关,并试着放下欲望。我们知道掉举和自我形象有关,也就是希望在世上占一席位,被人欣赏,这些想法是没有必要的。由于其他人都很努力的去建立自我形象,所以要有这种特别的见解是相当难的。
放下五盖并非指把它们根除,使五盖永远消失。我们可以把五盖视为花园中的杂草,如果我们不断除草,就削弱了根的力量,使它们不再遮蔽好的植物;当我们有足够的心力时,就可以根除五盖。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只是除草。
在每一节禅修前,我们自问:「现在我有没有瞋恚的念头?有疑惑吗?有掉举与恶作吗?我感到昏沉和想睡吗?我的心充满欲望吗?」如果有这五盖,就要把他们放下,用慈心和平静的心去对治,还要记得:修行是一无所获(nothing to gain),以及放下一切(everything to get rid of)。
第四章:初禅
已经说明能专注禅修的先决条件后,现在要讨论初禅(jhana)。有一点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所读的佛经是根据巴利经典(Pali Canon),而巴利经典是上座部佛教所根据的经典。所有读过巴利经典的人都知道:禅那是解脱道的一部份。正如其他在这部经中解释过的一样-五盖、守护根门、正念正知,都是解脱道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修行会带来喜悦和幸福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遵循每一个步骤,不可以因为某些部份太难,或是有人告诉我们某些部份是不必要的,而付之阙如,因为这只是个人的见解和意见而已。
佛陀指出了整条解脱道,能遵守他的教导是最安全和有效的。本经不是唯一讨论安止定的经典,还有许多经典讨论安止定。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许多禅修者有安止定(meditative absorptions)的经验,却不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是甚么。许多禅修者想寻找指导者,却徒劳无功。读了佛陀的开示后,我们可以依照佛陀所教的法来修,不过并不容易,大部份人都需要指导。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佛陀在经中的开示,佛陀说:「…(比丘)心知,已舍离五盖…。」这点非常重要,在初禅,只是暂时舍离五盖。五盖在安止定中无法生起,在打坐时,我们绝对不可以让五盖生起。由于五盖仍然潜伏在心中,所以我们不能让五盖生起。
我们要以慈心和悲心来禅修,心中没有疑惑,没有任何感官欲望,没有昏沉与睡眠,没有瞋心、掉举与恶作。在禅修时,一定要降伏五盖。事实上,我们自然会去克服五盖,因为如果有任何一盖生起,心会立刻变得激动(agitated),那时便无法禅修。相反的,如果我们有慈有悲,知足,并决心修定,不去想任何成果,那么便能降伏五盖。禅修会带来轻松感,即使只是暂时舍离五盖,我们也会感到很平静。
舍离五盖,观察己身者,便生欢喜,欢喜者生喜,怀喜者身安稳,身安稳便觉乐,乐则心入三昧。
这里的喜与乐仍然是世俗的层次,不是禅定的层次。巴利语有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两个层次,而英文就比较有限,欢喜(gladness)是一种放松和幸福的感觉,身体也会跟着安稳。有了安稳(tranquil)的身体,我们会感到喜悦;有了喜悦,我们的心会倾向专注,所有的禅修者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内心的喜悦是禅修的必要条件;没有喜悦便无法禅修。
这里所说的喜悦来自安稳的身体,而这种安稳的感觉来自一颗乐于禅修的心。喜悦生起的原因有很多:知道自己有能力依法修行;能够静静的打坐;或是身体健康。如果没有这些喜悦,尤其是乐于修行,那么当我们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时,便很容易忽视禅修。
没有喜悦,便无法入定,虽然佛陀经常提到这一点,而我们却很少听到。佛陀说:身心要先感到舒适才能禅修;只有心感到喜悦时,才能入定。如果我们知道为了甚么去修行,并且懂得欣赏自己的努力,单单了解这点便能带来喜悦。
以上所说的是pamoda,即世俗的喜悦,还不是sukha,即禅定的喜悦。一旦能在没有五盖的情况下坐禅,整个身心都会感到平静,仿佛身心合一一般,我们好像正在开展拥有巨大潜能的事业。佛陀继续说:
(比丘)舍离诸欲,离不善法…。
「舍离」(detach)这个字经常被误解,因为经中不会总是详细说明是「舍离诸欲,离不善法」。而有些经文只提到「透过离欲,进入初禅」,这经常被理解为我们应舍离正常的生活,到森林里住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森林中修行当然大有益处,却不是必要的。「舍离」在这里指舍离各种感官欲望或不善心所,也就是去除五盖,舍离五盖使我们有卸下重担的感觉。
有寻有伺,离生喜乐,住于初禅。
巴利文vitakka-vicara 经常被译为思考(thinking)及默想(pondering),这是不对的。所有禅修者都知道:如果心在思考和默想,根本不可能进入初禅。vitakka-vicara还有第二个意思,「寻」指将心导向禅修的对象;「伺」指将心持续放在禅修的对象上,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离生喜乐」,指已舍离诸欲,因而生起喜与乐。禅定中的喜与乐是同时生起的,「喜」在这里指欢喜,「乐」与喜同时生起,此时称之为sukha(乐),我们稍后会了解这是二禅的重点。在初禅,「喜」以许多方式和强度生起,可能是大喜或是轻微的喜;也可能有许多感受,如轻安、漂浮、扩张、扩大、激动,这些都是喜的感受,而且永远是喜悦的;这种状态也被译为趣味(interest),意指在这个阶段,我们对禅修兴致盎然。
此时,如果我们仍然在观呼吸,我们将错失良机。无论我们用的是哪一种禅修方法,都只是一把钥匙而已,把它插入钥匙孔,打开锁,越过门槛,登堂入室-此处是我们所了解的内在生命。我们会发现心中所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与身外之物有关的事。我们的心充满欲望、抗拒、本能反应、妄念、计划、希望、理念和各种观点。当我们的心变得专注,并感受到喜悦时,我们便能了解这个事实。
我们也知道这些感受一直伴着我们,我们没有刻意使这些感受生起;能够了解这点已经很不容易。这些感受一直都在心里,只是心中的风暴使我们无法觉知到这些感受。一旦我们有观察这些感受的能力,大部份的感官欲望和贪欲都会消失。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想要的,而这跟外在环境无关,也不会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外境,因为这是无济于事的。
初禅的体验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转变,然而,如果我们不继续禅修,我们将无法获得足够的禅修经验,内观智慧也无法生起。
(比丘)舍离诸欲,而生喜乐,润泽其身,周遍盈满;全身到处,无不充满,因离欲而生之喜乐。
如果我们只是身体某个部位感受到喜,那么我们必须把喜扩大,让整个身体都充满喜悦。虽然这里提到身体的感受,却不是平日熟悉的那种感受。这种「喜」与极度愉快的感官接触类似,却不尽相同,它比感官接触来得微妙,并更能使人满足。我们可以控制它,只要掌握禅修的技巧,我们可以随时让这些感受生起,而且时间要多长,都可以自己决定。所有精通禅那的人都有这种能力,他们可以在四禅八定中,从任何一种禅那到另一种禅那,不一定要按照次序;也可以决定进入和离开的时间。当然这些都是在较高的禅修阶段才能达到。
(比丘)入住初禅,因此先灭欲想,是时,生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perception)。
在这里,我们知道情欲(lust)在初禅已经消失,当身体有「喜」的感受,情欲就不会生起,我们对所拥有的东西已经心满意足,当然,欲望仍会伺机而起。如果从禅修中获得的内观智慧越来越深,我们进入禅那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欲望生起的机会也越少。
Lust通常指情欲,是所有感官欲望中最强的,也因此使许多人的生活非常混乱。强烈的欲望会使人丧失理智,所以找出对治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当内观智慧生起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渴求的一切早已在心中。经验一再证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放下情欲;即使不是完全放下,至少不会再干扰我们。
…是时,生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
「真实」意指我们真正感受到喜与乐。微妙(subtle)用来形容前四个禅那,它们是微细、微妙的禅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类似的心境,只是比较粗糙。我们的喜与乐经常要依靠外境才会生起,我们无法使喜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起。通常,一旦离开使我们快乐的外境,也会失去知足和满足感。在禅那,不会发生这种事。由于禅那中的喜与乐是微妙的,而此时的满足感也会持续不断。
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随时进入禅那;当进一步向二禅、三禅和四禅迈进时,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过这种微妙的感觉,只是比较粗糙和不圆满,它们是短暂的,无法随心所欲的一再生起;而我们只要坐下来,入定,便可以一再拥有禅那的喜与乐。对心来说,以这种方式入定有很大的裨益,因为禅那可以消除妄念;所有的希望、计划、担忧、恐惧、喜爱、厌恶都会放下,这是放松的好方法,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
「…(比丘)心知,有喜与乐…」也就是说,禅修者把注意力放在喜乐上。佛陀接着说:「如是由修习,故想(perceptions)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布咤婆楼曾问佛陀有关「增上想灭」(the extinction of higher consciousness)的问题。他想知道:识如何生起,以及如何达到无意识。布咤婆楼说:他听说有四种方法可以达到无意识,但佛陀指出这些方法都是不正确的。佛陀说:「有因有缘,人之想生;有因有缘,人之想灭。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佛陀接着教导布咤婆楼如何使心清净,并因此得以进入初禅的方法。在这境界中,微妙的喜、乐想(perception)会生起;当心离开禅那,喜乐便消失,这是佛陀给布咤婆楼的回答。佛陀接着举了一个譬喻来解释初禅的感受,从这个譬喻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肥皂是怎样制造的。
譬如善巧浴仆,或其弟子,于盥浴器,而撒澡豆,以水混合,澡豆受润,因润散碎,以一铁片,塑造肥皂,由小成大,以油围之,以至周遍,无不浸泡。比丘亦复如是,因离欲而生之喜乐,亦充满浸润全身;因离欲而生之喜乐,遍满全身。
这个精彩的譬喻告诉我们:初禅的喜与乐应该是全身到处无不充满。要切记:打坐时,不可以让五盖中的任何一盖在心中生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观察自己的心,要以正念去觉知自己心念,不要让心去寻求满足欲望的方法。
无论是自主或不自主(impulsive)的身体动作,我们都应该保持正念和持续观察身体的动作,此时,心已经开始去除五盖了。打坐时,如果五盖已经不存在,那么,没有理由不能入定。一旦心想:「我要入定;我应该可以做到;或许我可以试试其他方法。」那么我们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应该单纯的去「做」,心中没有任何妄念,所有的妄念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心想出来的,所以不能反映真相。实相(truth)则完全不同,透过各种禅定的境界,我们会更接近实相。当然,除了禅定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至少我们可以透过修定来提升自己的心。
每次禅那结束时,以及在每一节好的禅修后,我们应该做三件事:首先要知道出定时,所有喜乐的心境都会消失,禅修者应该观察整个消失的过程,并知道喜乐也是无常的,不要千篇一律的说「无常」就算了;有些人听过和说过「无常」无数次,以至忘了这个词的意思,只是人云亦云的说:「一切都是无常的。」观察可意的境界如何消失,重要的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教义(teaching)的精神,这必须亲自去体验。我们可以读上千本的书,可以背上千首的偈颂,这些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益处,智慧只在亲身体验中生起,别无他法。
我们每时每刻都有体验,如果我们对所体验的事物有正确的了解,我们早就开悟了。例如,我们在每一次的呼吸中体会到无常,可是许多人对未来仍怀有无数的妄念。我们不了解只有当下这一刻才是真实的,未来和过去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当下是可以把握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假相。
我们都知道念头是无常的,会自然生起和消失。事实上,我们宁可念头不要生起,因为我们希望能入定,可是我们又相信:「是我在想,这些是我的念头。」我们应该观察这种想法。通常,当我们拥有某样东西,我们会有管辖权,然而,所有我们现在和过去「所拥有的」念头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拥有这些念头的「我」哪里去了?是否消失了?还是不断「拥有」新的念头?哪个「我」才是真的?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每当新的念头消失时,那个「我」又到哪里去了?前后的念头之间会有间隔,那时的「我」又在何处?是度假去了吗?我们如何把它带回来?当然是透过不停的想。
这个被误解的经验是产生「我」的假象的因。退出禅那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要知道禅那是无常的,同时也要知道念头、情绪、呼吸、以及身体都是无常的。
禅修后第二件要做的事是,扼要重述刚才的经验:怎样入定?用甚么方法?方法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对你有用的便是好方法。人们执着某种特定的禅法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对他们而言,这种方法很有效,行得通,因此认为其他人也应该采用。这是不对的,由于每个人的根器不同,适合某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他人。例如,有些人发现慈心禅很容易使他们入定。如果慈心禅修持得法,一股强烈的感受会生起,通常从胸口,这是很舒服、很温暖的身体感受。有时,除了温暖外,还会感到喜与乐。一旦有任何感觉生起,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感觉上;较强烈的感觉是与身体有关的,也是我们应该观察的地方。
只要能够入定,用甚么方法都一样。那时,我们才可以说:「我在禅修。」在此之前只能说:我在修习某种法门。虽然我们很少去分别两者的不同,但是佛陀早已告诉我们。
有些人透过修习扫瞄观察(sweeping exercise)来修定,如果修持得法,入定时,有一股非常喜乐的感受会生起,此时,应该停止观察,把注意力放在喜乐的感受上,然后,如佛陀所说的,再把这种感受扩大到全身。
另一个方法是修习遍处(kasinas),即颜色遍。如果我们很容易就观想出某种颜色,那么,我们可以观想一个圆的色盘,把它放大,并完全融入,这也可以使我们进入初禅,这是修习遍处禅(kasina meditation)的目的。
或是修习数息观,当呼吸变得微细,光便会出现,也可以把光扩大到全身。如果我们能使这种光持续一段时间,这光不但会围绕我们,而且一股非常愉悦的感觉会生起。
有许多方法可以入定,当然我们不需要在一次禅坐中使用所有的方法。如果发现慈心禅很适合,就用来修定;假如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观想颜色,而在观呼吸时,颜色障碍了修习数息观,那么我们应该改为修习遍处禅。同样的,如果观察身体很容易专注,便应该用这种方法,所以用哪种方法修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坐禅时,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有极大的潜力去证悟。
所有有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禅修者都能进入禅那,心自然会入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禅修者都渴望能入定,他们或许不知道禅那这个词的意思,或安止定是什么,却渴望能从永无休止的念头中解脱出来。虽然有时这种渇望是不自觉的,却有可能。当一个没有成见的人初次听到禅那时,通常的反应是:「啊!我知道某些东西是存在的(there was something)。」有时,初次体验禅那时,我们记得原来小时候曾有这种经验。小孩子通常会自然而然的体验禅那,这比想象中更普遍。在成长的过程中,上学、家庭、性爱都会干扰我们,于是这些事便被遗忘。成长后,在我们饱受众苦后,去禅修并达到初禅,记忆又会重现。
当佛陀仍然是菩萨悉达多.乔达摩(Gotama,或译为瞿昙)时,他离开皇宫和家人到森林禅修,他从某位老师处学习前七种禅那,并且一进入初禅,就记起他在十二岁时,曾进入初禅。故事与佛陀的父亲有关: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是个小国的统治者。在春天来临时,他们有春耕节,根据传统,国王应该先翻土,净饭王带着十二岁的太子去参加春耕节,太子要和国王一起扶着犁,一人扶一边。然而当典礼时间到了,却找不到太子,净饭王派一位大臣去找,发现太子在一棵树下打坐,而且非常专注,浑然忘我;为了不打扰太子入定,大臣回去告诉净饭王,净饭王说:他会自已翻土。
稍后,在十二到二十九岁期间,太子沉迷在各种欲乐中,他结婚了,并育有一子。最后,他决心要去解决人类受苦的困境,于是他去森林禅修。由于他在前世和小时候都有进入禅那的经验,所以很容易就能入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太子般容易入定,然而,年幼时曾有禅那经验的禅修者,的确比较容易入定,而我们就必须更加努力,去上一些训练耐心和意志力的课。
佛陀从不曾说:初禅不会引起执着。这种观念是佛陀涅盘数百年后,注释家所提出的。禅那的体验不但不会引起执着,而且能使禅修者有充沛的活力和迫切的想去禅修,因为我们会发现禅那的心和世俗的心大不相同。即使迫切感没有生起,也会有「这不可能是全部」的想法,而会有想一窥究竟的想法。所有的智者都应该知道:禅修的目的不只是获得乐受而已。虽然感到快乐,然而我们知道禅修不只于此,所以会颇有兴趣的继续禅修。
此时,禅那的心是纯净和明洁的,这点非常重要,纯净的心是禅那最可贵的收获之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了解纯净。首先,心中没有任何五盖和烦恼;其次,它可以带来清明。当某种东西是纯净的,它也是清明的。如果窗子是脏的,那么我们很难看到窗外的景色;而擦干净后,我们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我们需要清明的心来禅修,以获得内观智慧。
纯净的心来自勤奋和持续的修行,来自「自我了解」和知道自己该做些甚么。清明的心是真正要追求的,因为清明的心使我们能了解我们的经验。一旦有了清明的心,我们会尽可能不再污染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清明的心如珍宝一般,所以会保持警觉,以免遗失。这颗纯净和清明的心,可以粉碎一切迷惑、假象,让我们看到世间的究竟实相(absolute truth)。
为了证得佛陀所教导的深湛的内观智慧,我们需要一颗清明的心。清明的心来自绝对的专注,此时没有任何妄念;只要有妄念,表示心还在世俗的层次,此时,我们只能看到心中的妄念。
第三步是:在每一节的禅修后,我们应该观察禅修的体验,看看是否有新的观智生起。这种观智特别有启发性,因为是从亲身体验中生起的。佛陀是个非常实际的导师,他教导前四个禅那时只用数字表示,而不替它们命名,以免后人故做解人,依文解意,我们只需依教奉行即可;而从第五禅到第八禅都有名称,我们稍后会讨论。
禅修时,自然可以达到这种心识境界。我们可以从基督教和其他神秘主义教派的作品中读到有关禅那的记载。他们所用的术语或许和我们的不同,而经验却是一样的。《七宝楼台》(Interior Castle)是指导修女们的书,在书中,作者圣德雷莎(St. Teresa of Avila)提到七种禅那,她以梦幻的(visionary)方式叙述,而今恐怕很少人能解读。由于她的叙述非常详尽,让人觉得这些经验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相反的,佛陀的教导就非常实际,不可能让人误解,因为佛陀的开示是针对每个人。其他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学家,例如Meister Eckhart和Francisco de Osuna也修习禅定,当然他们对禅那的描述也各不相同。
我们处在科技主导的时代,而不是宗教主导的时代,禅那的方法渐渐失传了,但也不一定就此消失。借着佛陀所留下的「法」,我们很幸运可以接触到这些禅修方法。
有些人能够在没有人指导下入定,这是心专注一境的结果,也有人在大喜或极度紧张中进入禅定,而且并不罕见;而其他人进入禅定只是透过专注,专注于所缘境。
禅修是一门心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mind),既然是科学,就可以解说和重复验证,而且必须包括所有的心境。我们熟悉一些世俗的心,如思考、判断、快乐、不悦、渴求、排斥等。世俗的心经常处于二元状态,在二元状态中,「我们」和「外界」是对立的。如果禅修无法带来不同的体验,那么也无法使人满足。
透过禅那,我们所体验到的高层次的心识状
态,显示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虽然有这个身体和心,我们仍然可以超越;这是为何佛陀教导每个人,透过禅那来证得内观智慧的原因。在所有叙述解脱道的经文中,无不是从持戒开始,一直说到开悟为止,中间的禅那(jhanas)从来没有遗漏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我们打坐不是想要获得喜乐的感受;相反的,我们只是遵循我们所选的方法去禅修-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方法,并持之以恒,这样就够了。
第五章
第二禅和第三禅
在这部经中,佛陀对布咤婆楼说明整条解脱道:首先是持戒,其次是守护诸根、正念正知、知足,去除五盖,以上都做到了,禅修者才能进入初禅,这就像地图一样,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到达目的地。所有人都知道如何使用地图,如果我们不按照地图上的标志走,就会迷路,假设有人要从洛杉矶开车到纽约,只看纽约的地图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一份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地图才有用,而且还要以英里来标示到达目的地的里程。
讨论过初禅后,佛陀继续教导二禅。在以下的经文中,寻、伺被译为思考和默想(pondering)。
复有比丘,灭除寻伺,内心寂静安详,住心一境,此时无寻无伺,沉浸在由禅定所生之喜乐,入第二禅。
刚开始,我们的心专注在呼吸上,然后继续观察出入息;二禅不需要这两种工夫(即寻与伺)。由于进入初禅时,心已有足够的定力,能保持稳定。之前,心仍然很不稳定,必须透过禅修才能稳定下来。在开始阶段,心会跑掉,不能专注在禅修的目标上,所以要不断的把心专注和固定在禅修的所缘境上。在这个过程中,喜乐的感受会消失;事实上,是我们的定力消失,心的感受依然存在,只是没有任何感受而已。
我们可以专注在喜乐上,而不是专注在呼吸或慈心禅或其他禅修的目标上,我们可以把心只放在感受上。当知道身体某一部位有最强的感受时,便直接观察这个部位的感受。我们不是在观察身体,而是观察身体的乐受,因为乐受在身上,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部位。如果不能掌握这个方法,我们必须从寻、伺开始,行不行得通,要看禅修者的定力。
当训练有素时,我们可以专注在乐受,并由此进入二禅。我们要在乐受中停留一段时间,完全投入,并觉知乐受的生起,大约十到十五分钟就够了,此时,心必须安止不动;而不再专注于乐受,必须刻意去做。在另一部经中,佛陀指出,由于知道身体的乐受仍然是粗糙的,禅修者仍需追求更高的层次:心的感受(emotions)。
一旦放下身体的乐受,我们会专注在内心的喜悦上。这股喜悦已在心中,我们只是改变专注的对象而已。此时,喜仍然存在,这时感到身体很轻,身体的感受消失了,仿佛没有重量。如果有足够的定力,身体不会不舒服,也不会疼痛。当然,退出禅那后,这些苦受可能会生起。此时,喜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乐」能对治掉举和恶作,所以乐(sukha)能使心平静。如果我们没有乐受,有时试着轻轻的说「乐」这个字,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禅悦。当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字时,便会进入禅定,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效,有些人发现这样会妨碍入定。
喜与乐都有兴奋(excitement)的成份,我们会觉得喜乐好像在头部的某处,当然这只是印象而已。当我们刚进入初禅时,会有强烈的兴奋感,会想说出心中的感受。当我们培养禅修的习惯后,最初的兴奋感会消失,而会有很微细的兴奋感。我们还未达到真正的平静,因此必须一步一步的朝着目标前进,前一步是下一步的因,每一步都是因与果。透过禅定会生起喜悦的感受;由喜(delight)生起乐(joy);当我们体会到如此殊胜的喜悦,怎么可能没有乐受?大部份的人从未体验过这种内在的乐,因为他们必须依靠感官接触才会快乐。所以如果能找到内在的喜乐,我们就能获得许多观智。
…是时,先灭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起由定所生之喜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自知心有喜乐。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经中的想(perception)其实是意识(consciousness)的意思,所以这部经也叫《心识的各种境界》(States of Consciousness)。在此处,佛陀说:透过修习,可以生起某些意识;透过修习,可以灭除某些意识(即:「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我们知道:心有时快乐,有时痛苦,经常想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或想舍弃我们已经有的,因此没有完全平静和喜悦的感受,或许我们不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我们平日为了谋生,以及和人打交道时的心识状态永远是二元的;一边是「我」想要某些东西,另一边是和「我」相对的外在世界,或是和「我」相对的你。「我」永远与外在的人事对立,这样,心不可能平静下来。
我们都熟悉这些心境,大部份的人认为只此而已,由于这种信念,他们就向外追求满足和快乐。开始禅修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全然不同的心识状态。这个理解对人有极大的冲击;之后,我们会深信不疑。修行越久,对这些心识状态越了解,大悲心就会生起。这种高超的心境与日常的心识状态比起来,实在高尚多了,因此我们会充满悲心,想去帮助他人,让别人也能解脱痛苦。
佛陀在三十五岁开悟,在八十岁时去世,他一生都在帮助别人,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经典上记载着,佛陀每天都在教导,即使天气险恶,身体有恙也不例外,不论到哪里,无论路途有多远,佛陀都是走路去的,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是用牛或马拉的,佛陀不忍心把自己的体重让动物去承受,所以佛陀从不乘车。现在仍有一条戒律禁止出家人乘坐由动物拉的交通工具。经上也记载佛陀每天早上都会禅修,并「张开悲心的网」,意指佛陀用天眼去观察有谁愿意听闻法。佛陀说:「眼中只有微尘」的人不多,由于知道他们会接受「法」(Dhamma),所以前往渡化。
初禅有「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也就是说,进入初禅有「从舍离感官欲望、五盖和其他不善心而生的喜乐」;在二禅则有「从禅定中所生的喜乐」(定生喜乐),也就是说,进入二禅,定力会加深。在初禅,偶而会有微细的妄念生起,也会听到声音,只是没有平日清楚,这表示声音对心的影响非常小。在二禅,声音的影响更小,我们好像坐在玻璃圆罩内,所有外面的声音都被隔开了,干扰也减少许多。随着禅那的进步,定力会越来越强,渐渐的会住心一境。
这样的专注能使心清净,而心清净会带来清明,前者引生后者。有时,佛陀的教法被称为因果的教法,因为他的指导非常清楚,明确,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解脱道;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因,我们很容易了解,而「了解佛陀所说的法」是修行的起点。虽然了解佛陀所说的法,无法立刻带来平静和观智(insight),但不了解「法」,就不可能进步;了解「法」,才有动力去修行,此外还要有一颗开阔的心,假如心不开阔,所有佛法的知识都没有用处。我们说法可以说得舌灿莲花,可以写出博学多闻的作品,但永远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如果不打开心扉,便无法了解「法」。了解「法」,便能生起信心,使我们乐于修行。
退出禅那或在任何好的禅修后,我们要知道坐禅后的三件事,首先是观察所有经验都是无常的;其次是记得通往禅定的道路;第三是:我们要自问:「从这个经验中我学到了甚么?以及观智有没有生起」。
进入初禅,禅修者有喜乐的感受,心立刻体验到一种高超的、广阔的心识状态;这种心识状态迥异于「想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消费者心态。广大的心识使人了解到:生命中有许多境界远超过感官所能体验到的。即使是最愉快、最微妙的感官接触,例如鲜花、彩虹、落日、诗等,虽然这些景物没有任何不善,因为都是外在的,要依赖外境快乐才会生起,然而,外境无法永远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认为落日余辉令人陶醉,事实上,是心沉醉在落日而生起愉悦,所以是心使自己陶醉,而非外境。我们经常认为快乐来自外境,然而外境只是引起感官接触,使我们的心完全专注,以致浑然忘我,在那一刻失去了「我」的感觉,此时,没有「人」在想:「我要这个;我想要有这个东西。」一旦外境(如落日)消失了,喜乐也会消失,而「我」又恢复原状。随着所生起的念头:「我」要去追寻那醉人的落日,因为落日能带来乐趣。这个例子说明事实是: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需要证悟,只是我们不完全了解这些经验而已。我们需要「法」(Dhamma)来指导我们,然后才能如实的观察事物。
我们知道有各种层次的心识,也知道所有的喜悦都来自内心,不假外求,是内心的清净和专注使我们体验到这种喜悦。由此可知,我们所追求的,心中本自具足。大部份的人向外追求满足、幸福和快乐,他们不知道感官接触的快乐必须依靠外境,所以是不可靠的。
在二禅,当我们体会到喜,我们知道:这种喜比以前所体验到的更微细,而且毋须依靠外境。此时,整个人沈浸在喜悦中,这是感官接触所没有的。禅修者知道:进入二禅可证得第二种观智,此后毋须再追求愉快的感官接触-虽然这种愉快的感官接触仍会发生,而我们的生活也会有极大的改变。追求感官欲望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无论能否得到所想要的东西,都不免受苦,例如只得到一部份,或有人从中作梗。
禅那会大大的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会把禅修的经验融入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依然如常运作,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我们会品尝、触、嗅、想,然而我们不会无止尽的追求感官之娱。
长期的禅修会使感官更敏锐,禅修者在长期禅修后,发现大自然比以前更绿,天空也变得更蓝,当然,天空和叶子并没有改变,而是受觉变得比较敏锐。此时,禅修者不会追求感官之娱,也不执着或想拥有这些乐受,禅修者自有禅悦,没有丝毫欲望,所以才会有一颗清明的心。通常,我们从未注意到感官之娱所带来的苦,这是执着所产生的苦,想要拥有所引起的苦。在禅修时,我们只有单纯的感官接触,不会执着外在的事物,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不需要向外追求内心已有的东西。
此时,内心的平静仍未达到不可动摇的境界,却足够为日常生活带来宁静、轻安的感觉。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或去任何地方,当然,我们仍会做某些事,事实上,我们会做得比以前更好,因为我们不再执着结果如何,更明确的说,是不执着「快乐来自成果(result)」这个观念。我们去做,是因为事情需要有人做,我们会轻松的做,完全不会紧张。我们知道:有比世俗之乐更美妙、更微妙、更大的快乐。我们不是鄙视或弃绝世间,而是对世间不再有任何期望。既然没有期望,当然就没有失望。此时,与任何人都能融洽相处。
佛陀在《沙门果经》(Samabbaphala)中提到二禅:
(比丘)由定所生之喜乐,润泽其身,周遍充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定生喜乐。
我们千万不要怀疑喜乐如何生起。喜乐都是心所(mental concomitants),却在身体出现,例如,我们体验到的乐是在胸口处,这是修行的心。喜乐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感受,而我们却指出它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我们必须透过这身心相关的地方才能有所体验,别无他法。在二禅,「喜」在幕后(background),而「乐」则在幕前(foreground),并从头到脚趾,充满全身。修慈心禅时,乐也是从头到脚趾,遍满全身。假如我们能够在修慈心禅时做到这点,便更容易进入二禅。如同初禅一般,佛陀也为二禅举了譬喻:
譬如有水,从深泉涌出,其水不从东来,不从西来,不从北来,不从南来,而时有骤雨。由此深泉涌出凉水,以此凉水,润渍深泉,周遍盈满,此泉之水,无不遍满。比丘亦复如是,定生喜乐,润泽其身,周遍充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由定所生之喜乐。
这段经文很有用,因为通常只在胸口处感受到乐,然而我们可以扩大这乐受,使喜乐充满全身,只有此时,对二禅才有完整的体验。当我们全身充满喜乐时,这时我们才知道:世间的乐无法与二禅之乐相比。因为二禅的喜乐是大喜,让人有满足感,也因此,我们的心境改变了。我们发现:我们不依靠外境也可以如此快乐,这种内心的喜悦使我们充满信心,并有一种解脱感,也使人变得诚实、和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下一步:三禅。
由于内心充满禅悦,这种喜乐可以对治五盖中的掉举与恶作,因此非常满足。这种满足感和前面所说的不同,为了能好好禅修,我们必须对所处的环境感到满足,感谢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感到轻松和满足。我们必须刻意去想生命的某些特质,并去观察这些特质,此处的满足感是相当不同的特质,这种满足感来自禅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一直想要的-充满喜悦。
无论禅悦是多么让人喜悦,多么让人满足,在一段时间后,我们仍要放下这种大喜,我们会有心往下沉的感觉,这只是一种感觉,不是真的往下沉。初禅和二禅好像在头部发生,而三禅则有更深的感受。佛陀是这样形容三禅的:
复有比丘,离喜住「舍」,正念正知,以身受乐(身体有快乐的感受),如诸圣所说:「舍念乐住」,入第三禅。
在这段经文中,「舍」(equanimity)出现了,事实上「舍」是四禅的特征,所以有时很难去分辨三禅和四禅。修行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放下禅悦-喜与乐,是刻意的放下,而不是由于心不专注而让禅悦消失,果真如此,禅修会中止。这样修持比较好:先进入二禅,体会禅悦后,再放下心中的喜乐。在另一篇开示中,佛陀提到:禅修者在二禅所体验到的乐仍比较粗,所以要进入更微细、更微妙和更高的境界。
有些人很难放下二禅的喜乐,而有些人则未曾体验过,修行道上有各种障碍,只要持之以恒,就能究竟解脱。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训练自己的心,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耐心和毅力,有没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们一定要放下那种追求成果的情结(achievement syndrome)。为甚么呢?因为内心本自具足,毋须向外追求。
如果我们不专注,内心的喜悦便会消失。我们知道:这是另一个说明真相的例子,我们只能觉知心所专注的对象,此时,内心会感到轻松和满足;首先,平静和轻安会生起。「舍」(equanimity)指满足,满足就是「舍」。正念正知(clearly aware)是形容心一境性,这时,心完全觉知和警醒。「身体有快乐的感受」是所有禅那的特征,而且非常快乐。不同的是:初禅是身体的乐受,二禅是微妙的禅悦-内心的喜乐,而三禅的乐则来自知足和平静。
内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智慧已经生起,内观和智慧两者同时生起,而且是透过亲身体验才会生起。经中以吃芒果来譬喻。如果我们不曾吃过芒果,有人给我们非常详细正确的描述,甚至附上图片来说明「这就是芒果,以及它的味道如何」。我们可以欣赏芒果的图片和说明,却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除非亲自品尝。佛陀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由于得之太易,我们很容易忘失佛陀的教导。
由于内心的知足与平静,另一种观智可能生起,在禅修时,我们不要去想所发生的事,因为这涉及念头的生灭过程。一旦有了体验,观智会自然生起;我们知道:只要心无所求,心就会知足和平静,内观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的心有各种欲望,有些欲望相当微细,而有些则相当荒谬。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只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和伤害;而在三禅所生起的满足和平静,比欲望的满足要殊胜得多。了解这点后,我们就可以把欲望放下;放下了欲望,同时也舍弃了因想望(wanting)、掉举、想要获得和达到目的所产生的「苦」。
无愿(wishlessness)是一道通往开悟的门。怎样才能找到这道门?透过体验才能珍惜它的价值,至少要有短暂的体验。当然,三禅无法使人开悟,但却能带来平静和知足,这让我们体会到无愿的滋味。
「无愿」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我们可能已经净化某些欲望,然而我们知道:即使是最微细的欲望,也会使我们掉举(restless)。对「无愿」的体会,使我们「离苦的能力」大大增加,我们终于尝到芒果,无需问人或查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无愿,也知道「知足」指无愿无求。
在禅那,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由喜乐所生起的无愿,而在日常生活中就难多了。然而,透过不断的修习,直到「无愿」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就会一直有「无愿」的体验,而心会更习惯这种心态。
如果不加以应用,观智(insight)就会退失,正如学了一门外语却不练习一样,之后,当我们再度听到,就会记得我们曾学过这种语言,再勤奋努力,就可以回想起来。观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很快就会忘失。直到有人提起,我们才知道自己也曾有这种观智,这时,才会加以运用。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内观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练习,不断进步,那么,观智便成为我们的了(不会再忘失)。
佛教经常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另一种是法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Dhamma),是我们谈论究竟实相时所使用的语言。佛陀同时使用这两种语言,他谈论世俗的、日常发生的事,也解说究竟实相。我们必须知道两者的不同,知道何时使用哪种语言。当佛陀谈到禅那时,虽然他谈的是高层次的心识状态,而他所用的仍是世俗的语言,因为仍然有「我」在体验禅那。除非我们能改变心识状态,否则我们会发现很难了解这个层次的术语。
此时,先灭「定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生舍(equanimity)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舍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perceptions)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在这部经中,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一再出现,这是针对布咤婆楼和他最初的问题:「想或意识如何生起?如何灭去?」佛陀告诉他在各种禅那中意识的生灭过程。这段经文中的「舍」是一种满足感;而「乐」是潜在的,只有前两个禅那有乐受。当我们感到满足时,是不可能不快乐的。
佛陀以譬喻来说明三禅:
譬如青、红、白莲,一一莲池,诸莲皆生水中,皆长水中,皆浸水中,为水所养,此等诸莲,以水润渍,由顶至根,无不遍满其中。比丘亦复如是,其身无喜,以乐润泽,周遍充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无喜之乐。
佛陀所说的两个譬喻都提到「遍满」。在二禅,必须从头至脚,全身充满喜乐;而三禅则是充满「无喜之乐」或舍心。由于大部份的人不知道舍心的意思,所以用满足或平静来形容更贴切,而我们对满足和平静都有相同的认知。而三禅的平静,比我们在世间所体验到的任何事都来得伟大。
有趣的是,我们的内心都有这种平静,只是我们心中有许多「战争」,除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外,还有我们内心的冲突,以及家庭和工作环境的争执等。而平静本来就在心中,只需专注(concentrate)就能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即使在禅修时,很少人能够在禅修时发现心中的平静。只要我们能使内心平静,就能改变整个生命,甚至改变他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影响。即使是在山洞中禅修的行者也能透过意念影响世界,何况大部分的人都不住在山洞里,所以一定会互相影响。如果我们把内心的平静散发出来,其他人会感受到,也可能因而受益,甚至被吸引而想要效法他们。
此外,还有一种普遍意识 (a universal consciousness),所有人都是普遍意识的一部份。所有的心识都在普遍意识中,假如我们,无论一个、二个、十个,或是一百个人拥有平静的心,又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并改变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平静的心就会进入普遍意识中,而且经常如此。同样的,我们的心念进入普遍意识后,又会回到我们的心中,像是回音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可触及(can be touched)的内在体验,普遍意识就无法把平静送给我们。
佛法不是与世人无关,不是「只要我有平静的心就够了,即使这世界毁了也与我无关。」佛陀从来没有这种念头。佛陀从开悟那天开始,一直向人宣说解脱之道,结果佛法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并传到这里。
在这部经中,佛陀谈到心的统一(unity of mind)或心一境性,另外的意思是意识的统一 (unity of consciousness),这是在禅那中生起的非常微细的意识,这种意识使我们了解:人与人之间并非彼此分离的,我们都是互相关连的,都活在同一个世间。当我们对禅那的体验越深,这种觉知便成为一种经验。这种意识的统一能增长慈心和悲心,因为此时没有「我」与他人之间的隔阖,只有一颗平静的心,别无其他。
一旦心能够提升,并超越平常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通常是负面的,而且与分析、逻辑推理和知识有关。我们可以提升所有的心识,并去改变环境,而不是让环境来改变我们。以下的观念是严重的错误,也是一般人常有的观念,也就是认为我和环境是对立的,我要操纵环境,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与外境根本没有界限,我与他人、与整个自然环境都没有界限。我们与他人与外在环境是互相依存的。如果我们想要有较少污染的环境,首先要有一颗较少污染的心,而这颗心有能力达到更高的心识境界。
以上所谈的心识境界,虽然不限于禅那中的境界,却奠基于禅那才会产生。
第六章:第四禅
虽然在禅修时,我们不一定能入定,然而知道禅修的心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及禅修的心如何改变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解脱道上我们只走了几小步,我们仍需了解整条解脱道,然后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目前的位置,继续解脱的旅程。
复有比丘,舍乐离苦,已灭忧喜,入第四禅,不苦不乐,舍念清净。
这段经文有时会被误解,认为前几个禅那有苦有忧伤(grief),而真正的意思是: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乐受和苦受,取而代之的是舍心和正念。如果要描述此时的禅那,以「心一境性」来代替「正念」会更贴切。事实上,「舍」是四禅的成果,心体验到寂静,当然此时不会有「这是舍心」的念头,因为一旦有这种念头,我们的心便不再平静。
我以一口井来比较三禅和四禅的不同,三禅就如我们坐在井边,把头伸进比井边安静得多的井内;要体验四禅,就要到井底。在不同阶段的禅那,我们会体验到不同程度的平静,这是很明显的。禅那也可以比喻成把身体完全浸在海里,而井的譬喻更能突显出禅那境界不断的深化。在三禅,平静已经很明显,禅修者仍会听到声音,除非声音非常大,否则不受干扰。当心越来越专注,声音会消失,因为心完全专注在寂止上,所以不受任何干扰。
在禅修以外的时段,我们不可能有这些体验,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平静和满足的时候,但总会受到外界干扰,我们不断的看、听、尝、触、嗅和想。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单纯的听或看,事实上,心会吸收和消化我们所看到和所听到的,此时,心无法完全寂止。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的寂止,完全的平静,观察者必须与被观察的对象暂时融合,合而为一,除了这个方法外,别无他法进入四禅。
前三个禅那,在某种程度上,观察者和所缘境是对立的;在四禅,这种对立不存在,因为观察者非常微细,让人感受不到有「人」的存在,唯一可形容这种状态的词,是心已经沈入「寂止」中。事实上,观察者并未真正消失,只有在证果时才会消失,稍后我们会谈到这点。说观察者与所缘境合而为一,意指在禅那期间,舍弃了我执-自我坚持(self- assertion),所以许多人怕进入深定,因为他们的自我在从中作梗。无论放下自我是多么的短暂、多么不彻底,对许多未曾禅修的人来说,是让人骇怕的,所以宁愿退出也不愿让心沉入寂止。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要紧,因为我们可以一再的尝试。这就像对自己的游泳技术没有把握,不敢到深水的地方去游一样。一旦我们有完全寂止的体验,我们会了解:只有暂时舍弃我执和「自我存在」的欲望,以及对任何境况的欲求,才能进入寂止状态,我们才会了解:舍弃自我是多么的美妙,以后会更想彻底舍弃我执。
四禅可以使心力大大增加,大多数人都过度劳心,白天不停的思考,晚上不停的作梦。心是非常珍贵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心相比,而我们偏偏不让心有片刻的休息。只有当「心」停止思考、没有反应,不再有情绪反应,不再观察外境时,心才能回复本来的清净。在前三个禅那,心只能瞥见这种境界;而在四禅,心能不受干扰的体验寂止的境界。经常修习四禅,能使内心更清净,心会更清明,也会更有力量。
强而有力的心是很难得的,大多数人的心都有习性,一听到甚么或读到甚么,心马上会有习惯的反应。如果接受某种特定的思考方式,心就会遵循这种方式。要能够独具慧眼、独立思考,并看透外在的事物是很难的;而四禅能强化心力,所以能看透外在事物的虚幻不实。
如果我们过度劳累,不睡觉,没有充分的休息,会发生甚么事?数日后,我们会非常衰弱,无法正常生活。而一谈到心,我们认为:即使从未让心休息,心仍能以最佳状态运作。佛陀称未经训练的心为「醒着睡觉」,这指心无法觉知到我们所碰到的事物,例如我们都会遇到无常和苦,如果我们想从中寻找体验者(experiencer),我们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真理,虽然我们有所体验,却无法识别(recognition)。
当我们退出四禅后,我们会有恢复精神的感觉,这是心的力量。一方面,我们让心休息来恢复精力;另一方面,暂时去除我执后,心会完全寂止,此时,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在四禅,心终于能够放假,回到本来的清静。通常我们放假后会比平日更累,不是吗?而四禅的假期就非常宁静。我们会放下一切引起我执的事物,这意味着我们了解「有自我」是错误的观念。此时我们已略尝解脱的滋味,而向道之心也会大大增强。
在四禅,我们更容易证得舍心。「舍」是七觉支的其中一支,是最高尚的情感。我们会经历不同层次的舍心,首先是当不如意的事发生时,不再激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应该有的反应,或是我们不想看起来很愚蠢,也可能是自我压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通了。长远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受影响,反正,一切事物都会消失、坏灭,此时,我们要让舍心生起。
佛陀曾谈过五神通(ariya iddhis)。Ariya是神圣的意思,而iddhis是神通。神通经常被形容为魔法般的神奇力量,例如可以瞬间将身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人问佛陀:是否有必要具有这些神通?佛陀说:「我会告诉你五种神通。」只是佛陀把「神通」的意思改变了,并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佛陀所说的五种神通是:第一,每当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我们要立即从中找到快乐的一面,不要让自己变得消极;以正面的心态来看待事物,此时,舍心便会生起。
第二种神通是,每当碰到快乐的事,能立刻看到它不快乐的一面,这样,我们才不会陷溺在欲望里,舍心才会生起。所有令人快乐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点-无常,我们必须记住这点。大部的人认为他们相当了解无常,也能接受生命中的无常,事实上,他们把无常给忘了,而且经常如此。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生命中的每一刻,无论是快乐或痛苦,只是永恒中的一剎那而已。为了去除贪欲,以及去除对令人快乐的事物的渴望,我们必须知道快乐有无常的一面。
第三种神通是,我们要从非常不喜欢的人事物中看到他们的可取之处。例如,假如有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我们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苦,因此也值得悲愍;他也同样追求幸福,也需要人帮忙。如果遇到逆境,我们以积极的观点来看,认为这也是学习的机会,如此才会心情开朗,才不会生气和变得消极。在修习一段时间后,舍心就会生起。
另外两个神通相当类似,指能同时看出可意和不可意(unpleasant)事物的正面和反面特质。第五种神通只有阿罗汉-即开悟的人才拥有,阿罗汉能毫不费力的同时看出事情的正反两面,而不会生起贪或瞋。佛陀时代,没有记载下来的经典,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而有些内容是重复的,这样比较容易记得。
以舍心、平静的心来面对自己的贪与瞋,这就是清净之道,这是第二种舍心。第三种舍心是不会退失的,因为我们对无常有深入的了解,如在指掌之间,而我执也被减轻到不会障碍舍心的生起。会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一切事物都是缘生缘灭,如此而已。如果所发生的事合我们的意,那很好;如果不合我们的意,那也无妨。这种舍心由内观生起,在四禅,舍心变得非常稳定。
每一种观智都以平静的心为基础;没有平静的心,便没有观智,所以在四禅所体验到的完全的寂止是观智必要的基础。从四禅所生起的观智,使我们了解:只有放下我执,这种舍心或完全的寂止才会生起。一旦我们有了这种体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让舍心生起,而毋须像以前那么费力的让舍心生起。
值得一提的是,舍心的远敌是兴奋、掉举和焦虑;而近敌是冷漠。冷漠经常被用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特别是那些曾经有不愉快的经验,曾经受到伤害,或是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他们常常会自我保护,不要有负面的情绪。为了避免沮丧、愤怒和嗔恨,他们压抑所有的情感,结果就变得冷漠。筑起冷漠这道墙后,他们不再感受到慈心和悲心;也不会把感情放进去,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放入感情,只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这种态度使他们把心扉关上。有时候,在观察全身时,会发现自己有冷漠的问题。如果以正念观察全身时,无法觉察胸口的感觉,这是一种障碍,感觉上像是碰到一道砖墙或水泥墙或非常坚硬的东西,我们好像穿上了盔甲,用来保护自己,在感情上不受伤害。
冷漠之所以被称为舍心的近敌,是因为两者非常相似,也很难分辨它们的异同。我们可能会认为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兴奋、激动和烦扰,这时才发现我们并未培养人性中良善的一面。舍心是透过内观生起,而冷漠则是一种自我保护,两者截然不同。由内观所生起的舍心,不会妨碍慈心和悲心的生起。舍心和冷漠也有相同之处,如果不求回报及没有任何期望,舍心和冷漠会很容易生起。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观察自己是否有冷漠的问题,这是很值得去做的。
是时先灭舍、乐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不苦不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不苦不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不苦不乐指没有情感,所以没有乐受和苦受。为了达到完全的寂止,即使是三禅的满足感和平静也要舍去。此时,我们的心已经被舍心和正念净化,因而能超越苦与乐。在我们体验到完全的寂止前,必须有一颗清净的心;在四禅,必须具足正念和心一境性,心如如不动。而在前三个禅那,心可能会轻微的动摇,而在四禅,心不会有丝毫的动摇。为了放下前三个禅那的乐受,我们必须有舍心;此时,乐受、喜悦、满足和平静全部都要舍去。
「具有不苦不乐之微妙真实想」是微妙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内心没有乐受或苦受,因为此时内心是寂止的。退出四禅后,我们会自问:「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才知道有不苦不乐的感受,有平衡的舍心。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说,而会说:「只有寂止,没有观察者。」也知道它的意思。
佛陀为四禅举了譬喻:
譬如有人,由顶至踵,以白净衣,被覆而坐,全身到处,惟白净衣,周遍全身。比丘亦复如是,纯净清明,充满其身;惟纯净清明,遍满全身。
千万不要误解「身」这个字,这是四禅的境界,虽说是「身」,却不是指身体的感受,而是全身的感觉。因为身体无法感受到舍心和正念,以及清明和清净,心才能感受到。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人沉入寂止的状态。如果以存在(being)来代替「身体」,经文的意思就会更清楚。
如是心寂静纯净,无有烦恼,离随烦恼,柔然将动,而恒安住于不动相中,尔时比丘,以心倾注于智见。
这些心的特质都是禅那的结果。在四禅,我们不会有这些体验,因为心是完全寂止和平静,不可能有任何念头。出定后,我们可以观察入定前后的心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境是如何改变的。
在其他的开示中,佛陀说:在退出三禅或其他禅那后,会「以心倾注于智见」;在四禅、五禅、六禅和七禅,出定后特别有用。「智见」指能如实观察一切事物,这是如实知见,透过亲身体验来了解实相。「知」指了知所看到的事物,「见」(vision)并非指看见一幅画的看见,而是把所体悟到的法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在进入禅那后,尤其是进入三禅后,心能够观察不同的实相,这是没有进入三禅的人所无法窥知的。这里的实相是指「无我」(no personal identity),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有实体的自我。有人会质疑说:「如果没有自我,那么是谁在禅修?」或者问:「感到心烦意乱的是谁?」问这种问题的人,不承认人们是生活在错误的观念中,也不认为这种错误的观念会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人认为:「既然我在这里,一定有『我』在。」这种认知属于世俗谛的层次,无法带来解脱和自在。
在这个层次,我们可以帮助自己,如果我们能净化我们的心念和情感,就能减少烦恼,而且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至于究竟解脱、完全自在,只有在了解佛法的最终目标后才能逐步接近。
从以上的引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想要有如实的「知、见」,必须有平静的心。如果心到处攀缘,是不可能看到实相,也不会了解一切只是身心的生灭现象,别无其他。我们在读过许多有关佛法的书后,在理智上接受「无我」的教义,然而要在内心深入体会「无我」,如果有一颗喜欢感官接触的心,喜欢到处攀缘的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反而会有「自我」是真实的这个假相。
透过禅修,我们会发现隐藏着的清净的心。清净的心没有任何执取,也不会想要「舍去」(getting away from)。这是清净的、透明的心,是普遍意识的一部份,这种心没有个体,没有任何欲望。如果我们的感官沉迷于外境,我们的心忙于反应外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些外境,我们的心仍须知道是何种外境。到了这个阶段,有了一颗平静的心,我们会有不同的内在体验。
如何去了解「无我」?佛陀接着说:
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种成,父母所生,粥饭所养,为无常、破坏、粉碎、断绝、坏灭之法。又我之意识依于此身,与此关联。
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地、水、火、风)所组成的。地大的特质是坚硬,作用是支持;火大即温度,作用是毁灭和生成;水大指液体,作用是凝聚;风大的特质是推动、支持,作用是移动。我们很容易看到身体是由四大组成,别无其他。「父母所生,粥饭所养」说的是因和果。身体也有生成的因,我们自己就是身体存在的因,我们以食物来滋养身体。出生时便有了身体,渇望继续生存是再度投生的因,没有贪欲便不会出生,人不会无缘无故出生的。宇宙万物根据自然法则在运作,一切井然有序,不会乱无章法。
当我们观察身体时,知道身体不是「我」。这怎么可能?身体就是我,只要照镜子就可以知道:「这是我啊!」有许多方法可以观察身体只是身体而已。首先,身体是无常的,身体不断在改变,会逐渐老化,这是身体无常的特性,大部份的人都能泰然接受这真相,只是认为身体不够美好而己。再以呼吸为例,如果我们憋气,想使呼吸变成「常」,会发生甚么事?大概会窒息,甚至死去,呼吸不可能是常的(permanent)。当我们修到正念现前,能深入观察身体的本质,所体验到的不只是身体的移动,而是发现身体不断的变化,因为细胞会不断坏死和重新分裂。科学家发现:人体细胞每七年会全部更换一次。还有更多的事实,例如,我们把食物吃了以后,会变成甚么?我们必须消化、吸收和排泄,进去又出来,身体内没有恒久不变的东西。我们一星期前吃的东西都会消失,我们必须一再的吸收养分。
人一旦相信「这是我的身体,身体就是我」,就永远无法减轻欲望,因为大部分的欲望和身体有关,花些时间来探究这点是值得的。我们认为可以使身体变得完美,有人说:身体不会罹患癌症,因为身体本身便是一个大的癌细胞。看看身体的排泄物,没有一样是吸引人的,为了保持健康所以必须排泄,没有人愿意把这些排泄物放回体内。如实的观察身体,身体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苦由身体产生,由于要不断满足身体的欲望,在许多方面,我们被身体所「困」。
我们知道身体由四大元素组成,也会观察身体中的四大元素。例如,我们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坚固和坚实(compactness),也可以站在树旁触摸坚硬的树干。当我们站在草地上,能感受到草上的露水和草的汁液;我们也可以在唾液、眼泪、汗水和血液中观察水大;我们可以在体温和地面的温暖中观察火大;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呼吸和脸上的微风来观察风大。我们可以观察风如何吹动云朵和树叶,从而知道身体是如何移动的。我们知道所有物质都是四大所成,我们的身体和其他物质并无不同,同样由四大元素所组成,所以佛陀说:四大是所有生命的基础。
知道身体的不完美是很重要的,这并非指要去排斥、否定身体,或认为:「如果我没有身体该有多好」,而是知道身体所带来的麻烦。透过了解无常,我们知道自己迟早会死,这不是理论上的了解,或希望死神暂时不会降临,这不是将来的事,而是时时刻刻会发生的事,我们随时都会去世;我们所有的念头、情感、呼吸和全身都不断的在变化。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不断的在生起和消失。了解这个真相,我们也同时了解:每天早上起床就等于再生一样,所以根本毋须去思考死后会发生的事,因为生灭现象每一刻都在发生。随着身体老化,这种再生变得越来越脆弱,直到完全停止,所以说死亡就在当下。
我们当中有人记得昨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在想甚么吗?不可能的,一点迹象也没有。我们连昨天的事都不记得,更遑论上一生的事。我们会记得生命中重要的或令人兴奋的事或情境,而这些是非常稀有的,其他的都成为历史,渐渐被遗忘。
身体是「无常、破坏、粉碎、断绝、坏灭之法」,我们很容易生病或遇上意外。要毁灭一副躯体一点也不难,随时都可能,尤其在战争、在致命的争执和意外中。
当我们思考佛陀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观察身体是否真的属于我们,还是由渴爱所生,四大所成,必须以食物来滋养,是无常的和容易被毁坏的?一旦发现这些都是因与果,发现身体并没有实体,就能了解:其实我们对身体的主宰力非常有限。没有人愿意生病、背痛、感冒或头痛,然而谁也免不了。如果我们真的拥有自己的身体,怎么会让这些事发生?
另一个误解是: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身体就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这是目前流行的「新时代」思潮中的一项谬论。连佛陀都会生病去世,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死,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死。如果真的有人可以长生不老,为甚么从来没有人做到?从来没有事实,也没有任何宗教能使身体不毁坏。我们当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正如照顾自己的房子一样。无论我们将房子整理得多好,也不会把房子视为自己,或认为房子不用修理和永远不会毁坏,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这个身体好像我们的房子一般,我们应该尽力使它保持整齐清洁,仅此而已。我们永远无法使身体完美。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去观察这个身体,并自问:「是谁拥有这副躯体?它有甚么功能?为何身体会做那么多我不要它去做的事?」「又我之意识依于此身,与此关联。」这是内观的第一步,也就是了解人由身和心所组成,心又称为识。现在流行的新时代思潮又有另一个观念,认为身心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这种观念不但不可能,事实上,还会给人带来痛苦。因为如果身心真的是一体的,人就无法以舍心来面对身体的疼痛。这个观念的用意是好的,可是与事实相悖,没有用处。然而,的确有共相意识(unity consciousness),以共相意识来观察世间,我们会发现:我们与一切众生共存在宇宙中,并没有人我之别,物我之分。要证到这个境界,只有当我们放下虚妄不实的自我观时,才有可能。
身与心是分开的,却互相依存,身心相互依存是人类的特质,身体带着心到处跑。虽然无色界的众生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身体,这点稍后会论及。很不幸的,我们的心必须依赖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非常疼痛,心马上会变得烦燥、消极、厌恶或抗拒。如果感到很快乐,就会产生执着,想抓着不放。身体的感受会引起心理反应,然而,并不一定永远都是这样。佛陀经常说:未觉悟的人被两种东西所困扰:身与心;而觉悟的人只被一样东西所困扰:身体,因为觉悟者的心不再对外境有反应。我们有可能不受身体影响,然而对我们这些尚未开悟的众生而言,身与心仍然要相互依存。
当我们观察身体的四大元素时,我们是观察身体的结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四方面来观察心。在观察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身体并没有主宰者。首先是观察感官意识(sense-consciousness),也就是看、听、尝、触和嗅等五种感官;其次是观察由感官接触所生起的感受(受蕴),包括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第三个步骤是观察心的认知作用,也称为标明(labeling)作用,例如,当苦受生起时,心中所标明的是「痛苦」;第四是行蕴(mental formation),或反应;心感到痛苦时,一般的反应是:「我不喜欢」或「我一定要把它去除。」在这个阶段,能够觉知心的四个方面,观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感官接触、感受、认知和反应,这对我们的禅修非常有帮助。无论在禅修或在日常生活中,知道心的四个层面是非常重要的。佛陀教我们:要知道心的四个层面,对所了知的经验要有智、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身与心中根本没有「我」。「我」只是一种想法,一种观念,它深深的烙印在心里,我们周遭的人全都如此认为。
然而这个「我」不只是一种观念,它也能够引起贪与嗔,我们知道贪与嗔非常容易生起,我们与贪嗔共住,熟知贪与嗔,而贪与嗔无法引起快乐。修行时,我们不但要观察身体的四大,也要从四个层面来观察心,观察心念如何生起和消失。我们可以观察每一次的感官接触(一种味道、香味),也可以观察「触」如何引起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等。
大部份的人都能觉察到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感官接触和随后生起的心理反应:「这个看起来不错,我要这个。」或是:「这个不好,我不要。」心理反应是如此的快,以致于我们完全忽略了认知(想蕴)和反应(行蕴)两个步骤。正确的修行方法是:一旦观察到有心理反应,马上要回想它是感官接触所引起的;再去观察心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感官接触所引起的;然后再去观察心如何诠释-也就是心的标明作用,如骯脏、恶心、可口、无聊等;观察这两个错过的部分:感受和标明。现在,在心的四个层面中(即感官接触、感受、认知和反应)去找出是谁在感觉(senses)、感受、认知和反应。心会告诉我们:「是我在做这些事。」然而这种「假设的我」只是一种观念而已,哪来的「我」在做这些事?我们会发现:这四个层面是自然而然,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些事,而我们可以观察它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可以在这四个层面中的任何一点停止,尤其是在「认知」(标明)时,若在「认知」这个阶段停止,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外境可以没有反应。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心会说:「是我在做决定,是我决定这样做的。」现在,你可以去找这个「我」,只找到「决心」而已,而这是一种心理现象,并没有「我」在里头。我们要一再观察,因为在五蕴中隐藏着假象,即「我」的存在。有人认为这决心来自于他们的思考;有些则认为来自于他们的感受;其他人会认为来自观察者或是意志力(willpower)。我们可以自问:当心没有反应,没有观察者,没有意志力时,这个「我」在哪里?当这些「我的」(指感受、意志力等)不存在时,「我」又在哪里?在做什么?要了解究竟实相,必须有专注力和意愿,才能了解生命的最深层,而不是只探究表面的现象,如喜好或厌恶等。如果我们有长期喜好的与厌恶的事物,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超越喜欢与厌恶的解决之道。
在出定后,这种观察很有用;如果不禅修,可能会流于知性游戏(intellectual exercise),而心为了逃避这些问题,会乐于这种游戏,心不想观察,并急着告诉我们:「是的,对的,这样就好了。」如果我们只观察肤浅的层面,没有什么益处;相反的,当深入观察而导致开悟时,它的益处是非常大的,也就是类似「啊哈」的经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认为有一个「我」在修习,是「我」在说「啊哈!」;恍然大悟的是心,不是「我」。
佛陀以譬喻来说明在四禅所生起的观智:
譬如琉璃宝珠,美丽出色,八面玲珑,磨治莹明,明亮无瑕,具一切美相,以索贯之,索深青色,若深黄色,若赤红色,若纯白色,若淡黄色,有目之士,置掌而观,当知此琉璃珠…。比丘亦复如是,心寂静纯净,无有烦恼,离随烦恼,柔然将动,而恒安住于不动相,以心倾注于智见。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种成…,我之意识依存于此,与此关联。
观智如同一块完美无瑕的宝石一般,清澈、明亮、没有瑕疵。正如欣赏宝石需要好的视力,而要有观智则需要一颗纯净、专注的心。禅修时,所观察的对象必须和自己的内心有关。是心在观察:「谁拥有感官触觉?是谁在反应?」当我们观察时,必定与我们的内在感受有关,内心会一再的认为:「是我!」当我们如此认为时,我们应该进一步观察,虽然确实有这种想法,当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这是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就要继续观察四大,观察身体生起的原因和身体是无常的,观察我们必定会死去,观察身体的一种特质或所有的特质(指无常、苦、无我)。当心的四个层面按照次序生起时,我们也要观察这四个层面:「是谁在做这些事?为什么所做的常常与所希望的相反?为什么我想进入四禅,却发生这种事?」用这种方法,我们会慢慢了解佛陀所教导的法。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表面现象,我们将永远无法应用这些修行指导。佛陀说:如果我们能走完整条解脱道,就可以彻底解脱苦。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对佛陀所说的法会越来越有信心,也会依照他的指导继续我们的解脱之旅。
第七章:五禅、六禅
-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
西元五世纪,觉音论师(Buddhagosa)在《清净道论》中,为前四个禅那做了很贴切的譬喻:
有一个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他没有带水,感到越来越渴。终于,他看到远处有水池,他非常兴奋,充满喜悦。
「在沙漠中旅行,没有带水」并「感到越来越渴」指我们的内心追求喜乐、幸福及平静,这些是无法从外境获得的。「看到远方有水池,非常兴奋,充满喜悦」类似在初禅所体验到的感受,知道目标在望,虽然仍在远方,但很快就会到达目标。
后来,那人站在池边,知道这池水能除去口渴,感到非常欢喜。这是描述二禅的境界,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内在满足的边缘(brink)。然后,他走到水池,尽情喝水,感到非常满足,和刚才到处寻找池水的心境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三禅的体验。如果我们很长的时间没水喝,我们知道此时身心是多么苦恼。这个譬喻道出我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追求所渴望的东西时,内心总是烦躁不安。一旦找到我们所渴望的东西,那种心境可说是天壤之别,我们感到喜悦、满足。这种喜悦的心境不是佛陀所说的最终目标,但也只差一步。然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继续修行的动力,以及获得新的内观智慧。
现在,这位在沙漠中的旅人感到非常平静。之前,为了生存,他不断寻找水源,感到焦虑不安,他的口渴使他到处寻找水,现在,口渴已经解除,他走出水池,在树荫下躺着休息,从困顿中恢复过来。这种轻安和四禅的经验一样,不是睡着,而是完全的寂止,让心休息。
以上的譬喻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有时,我们无法觉察所发生的事。正如我们要生存离不开水一样,要使内心满足,也离不开喜悦和平静。我们无法觉察自己不停的在追求某些东西。心的掉举反映了这点,我们到处攀缘,结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观念,尝试不同的工作。无论我们想做什么,都反映出内心的渴求,我们希望能从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这些渴求。其实,我们所追求的就在心中,所以要解决内心的渴望,也只能在心上下工夫,而且快多了,因为这是我们能找到满足与喜悦的唯一所在。
四禅是进入无色界禅(the formless jhanas)的跳板,我们都有进入四无色界禅的能力,事实上,这些定境或可称为「平凡无奇」,虽然这不是开悟,却是开悟的基础,并能训练我们的心力。开悟不是简单的事,需要极大的心力,所以我们必须先打好基础。修习禅那需要耐心和坚忍不拔,最重要的是,要有无所求之心(not looking for any achievement or result)。
前四个禅那是色界禅,也有「微细物质禅那」的意思,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类似的境界,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圆满,而且必须依靠外境。我们都有类似色界禅的体验,因此比较容易了解这些禅那。所有这些定境(absorption states)都潜藏在心中,只是被我们的颠倒妄想和不断生灭的念头所障蔽。无论何种念头生起,「我是否必须入定」或「我必须做这」或「我不想做」,这些念头是没完没了的。这些「定」被我们的念头、情绪、反应、意见和观念所障蔽,这些我们所熟知的心理现象会障碍我们入定,直到我们了解,我们从不曾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满足,我们才会在禅修时把它们放下。当「我」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或是「我」想要有所成就或不想有成就。这些念头对禅修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把这包袱丢掉,心才会转到其他心识状态,这是佛陀向布咤婆楼解说的内容。我们都有意识(consciousness),因此都可以进入这种禅定的境界。
有关禅定的论述和言论有些是矛盾的,让人产生困惑。看了一些有关禅修的书籍,容易先入为主,会产生成见,妨碍禅修,所以没有接触任何禅修的论述反而更容易禅修。只要坐下来,放下心中的罣碍,心自然会静止下来,没有颠倒妄想,直到证入涅盘,让心体会涅盘之乐。在这之前,只要放下一切,心就能体验禅那的境界。我们甚至不说是「入」定,而是把各种念头放下,就像一只从水池里跳出来的狗,把水抖落一样,我们也把念头从心中抖落。
下一步是无色界定。初禅到四禅是色界禅那(rupa jhanas),接下来的是四种无色界禅那(arupa jhanas)。Rupa指形相(form),Arupa中的A指「非」或「不是」。这四种禅那是无形无相的,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般的心识状态下,不可能有无色界禅那的体验。事实上,未曾禅修的人会觉得这有点像神话,而禅修者即使没有无色界定的体验,也会有粗浅的了解。就像前面的篇章中所说的,前四个禅那和身体的感受或情感有关,而佛陀所举的譬喻全与身体有关,如佛陀提到全身遍满、沉浸在喜乐中;而在四禅,身体处于寂止状态,这都和感受有关。而无色界定,只有心境(mental states),没有任何情感或身体的感受,所以经中没有任何譬喻。禅修者要证入这种禅那,平日必须不断修习前四种禅那,直到心变得温顺、柔软、有弹性,不再顽固和抗拒,才能体验更高层次的无色界定。
佛陀是这样叙述五禅的:
复有比丘,超出所有色想,灭除障碍想,不起异想(perception of diversity),故达空间是无边的空无边处定,因此先灭色想,同时生起空无边处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惟有空无边处定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在四禅,我们不再有身体的感受,只觉察到心、感情、感受的寂止,所以到了第五禅的「超出所有色想-身体的感受」,我们毋须刻意去修便可以做到。而破除「障碍想」(all sense of resistence)就要刻意去破除才会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会以皮肤为限的身体为「我」,皮肤以外就不是「我」了,我们都很清楚自己所占的空间大小,这是我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我限定。在前四个禅那,这种「界限」已经被扩大到某种程度,不再以身体为限,至少,禅修者的思想观念不再僵化。
从四禅退出,如想进入「空无边处定」,我们可以观察当时心所感觉到的身体边界,并慢慢把它扩大。前面章节所提到的观四大,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陀说;「不起异想」,意指我们必须超越个体(singleness),如一个人、一间房子、一棵树、一座森林、一片天和地平线等。我们将事物视为个别的、有范围的,这种「异想」是人类的自然心态。巴利语papabca意为差异(diversity)或各式各样的。每一种物种都由无数的个体组成,人类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外表看起来有点不同,我们被这些差异,被不同的面孔所吸引。在森林里,我们欣赏每棵树的形状,看看树干或树叶,观察每棵树独特的地方,并感受它的美。同样的,我们也会仰望天空,欣赏明月和看单独的星星;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人,我们被某个脸孔所吸引,发现它是讨人喜欢的,或对某人感到厌烦。然而如果要进入空无边处定,就必须超越所有的个体及其差异。
有两种进入空无边处定的方法,我们可以同时用两种或只用其中一种,至于要用哪个,视我们在扩大心识时遇上多少困难而定。第一种方法是先观察身体的边界,再将这边界慢慢扩大到无穷尽的空间。假如在这个过程中遇上障碍,意识无法扩展,那么可以用第二种方法:观想森林、草原、山川、河流和海洋,再观想整个地球和天空,以及地平线,当我们观察到地平线时,再把它们放下,只剩下无尽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不起异想」。
去思考这些指导方法,看看佛陀所说的是否真实不虚也很有帮助。界限是真实存在的抑或只是光学上的幻象?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宇宙间根本没有固体粒子,只有不断离合的能量粒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往往听过就忘了。透过观察,我们知道事物的真相,也知道所有的界限都是心制造出来的,因此会放下对「异想」的执着。
佛陀所说的进入「空无边处」的两种方法是可以刻意去做的,毋须等待好运来临。透过修持空无边处定,心会扩大,大部份的人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即使是透过实验和研究而了解真相的科学家,也无法使它成为他们思想过程(thought processes)的一部分,只把它视为科学上的真相而已。然而,如果这是真理,那么这指我们的心,因为心是宇宙最根本的因素;当然这里的心不是指个人的、我们所熟知的心。一般人将自己的心局限于个人,无法观察到宇宙的真相;透过思考和禅修,我们可以把心扩大。心的局限越少,我们越能把心扩大,也越容易证到究竟实相。
通常我们所知道的与究竟实相无关,这种认知障蔽和扭曲了我们对究竟实相的了解。如果我们把心扩大,就能超越这些界限,我们都有这种潜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框框里,要尽可能的把心扩大。
在修习止禅后,尤其是任何禅那(jhanas)后,我们应该修习内观-智慧禅,这会有很大的利益。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佛陀开始讨论当时社会流行的四种错误的自我观。我们不要认为以下的古典经文和现代人毫无关系,事实上,佛陀所说的正是现代人所想的。
今有沙门或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此我为有色,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而身坏时,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布咤婆楼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自我就是人的身体,身体就是我。这种观念在现代是如此流行,有此观念的人多不胜数,在任何有关神秘经验的杂志都会发现,有这种观念的人相信,只要使身体变得完美,我们就是完美的人。然而,我们不可能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完美;其次,即使拥有完美的身体,而身体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只是觉得身体好了些,仅此而已。
一般人当然不会谈到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但所想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每次照镜子时,我们都会说:「这是我。」镜中人除了是我外,有可能是别人吗?我们经常看到镜中的「我」,且认定这就是「我」,这种想法是障碍想,会局限我们。身体从来不会真正满足,相反的,身体的欲望需要不断的满足,有时还会有颇荒唐的需求。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想想看如果打坐时,坐在坐垫上的只有心而没有身体,那会省了多少麻烦,禅修会变得多么美妙,从此背不再痛,腿不再麻,身体不再痒,不再打喷嚏。当然我们仍要专心,不过容易多了。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个大包袱,而我们竟然把这个包袱当成自己,我们知道这个执着是多么荒谬吗?为甚么我们要像布咤婆楼和他的朋友一样视臭皮囊为自我?
接下来是另一个错误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听起来似乎更伟大(grandiose):
或有人于此,作是说言:「汝所言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是天有色(躯体),属于欲界,养以段食。汝不知不见,予能知能见。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这种看法是将灵魂视为自我。当身体坏灭,这个「我」就消失了,但仍有另一个属于欲界的神我(divine self),在理智上我们可能不相信有这种神我,不过心里却怀疑可能有另一个自我在灵魂里,或有个灵魂在自我中。不论是哪种看法都和视身体为我大不相同。而灵魂我(soul-me)或许是好的,我们不承认我们有善恶两面。有些人认为灵魂是比较完美的,所以才是自我。即使我们在理智上否认灵魂为自我,内心却渴望:如果身体不是自我,至少自我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另一种见解是,不论人死后到哪里,自我都会快乐。
第三种错误的观念是:
或有人于此,作是说言:「汝言之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是天有色(躯体),由意念所生,具足四肢,诸养无缺。汝不知不见,予能知能见。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这段经文说的是由意念所生、微妙的、更高的
自我,不是灵魂,在印度教称为「梵我合一」。梵我(Atman)是绝对的自我,而非特定的自我。佛陀指出它的严重错误,并一再说明这些观念是错误的。这个「意所成我」(mind-made self)指的是较高的禅那经验,第一个是空无边处定,在这个禅那,心体验了无尽的空间,产生「我」融入空间的概念,所以说是心在制造自我。
所有「自我观」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无法放下一个观念,也就是在各种行为的背后,一定有「某人」在行动。我们会想:「是谁在做我所做的事?」会自问:「是谁在想我所想?是谁在反应我的感官接触?是谁想要我要的东西?一定有人在作主。」即使我们不再视身体为自我,要做到这点并不难,我们也会去找其他的自我,首先是视灵魂为自我,其次是执取超然的自我,或是把无色界定所体验到的心识状态视为自我,如空无边处定或识无边处定。
第四种错误的自我观是:
或有人作是说言:「汝言之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超出一切色想(bodily sensations),灭有对想(all sense of resistance),不起异想,故达空是无边之空无边处。汝不知不见,予能知能见。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这是共相之自我(self within unity)。如能进入第五禅,就能体验到无边的空间,以及统一的境界,此时,没有间隔,没有阻隔。当时流行的统一意识(unity-consciousness)其实也有部份属实。这种意识是指我们在观察时,不会执取观察者的意识为自我,意识好像旁观者一样,观察所发生的每个现象。如果我们视观察者为自我,我们就会视色身、灵魂或超然的我为自我,我们就会变得爱评论挑剔和厌恶某些人事。我们会被欲望所困,因为我们会希望能得到我们所观察的某些东西,或想摆脱某些事物。一旦有这种观念,我们就会视色身为自我,相信有灵魂或超越的自我。当我们有融合的经验,我们会认为已经将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除去,这就是与神合一的观念,或是印度教中的梵我合一。佛陀反对这个观点,因为「合一」表示有某人或某物进入这种合一的状态。
以上四种错误的自我观,仍然有一些「自我」的假象。而统一意识比独立意识(separation-consciousness)有价值,因为在统一意识中,我们能感受到慈心与悲心,因为如果众生皆是一体,有谁能恼害或激怒我们呢?此时,也去除了许多忧惧。当我们感到孤立时,才会有被周遭的人威胁的感觉,甚至畏惧死亡。当我们与万物合一时,无论我们称之为神我合一或梵我合一,或其他的形容词,我们的畏惧感会大为减少。然而仍有些许的自我感,是这种自我感与更高的理想(higher ideal)合一。
以上四种错误的自我观值得我们去深思,看看自己是否执取其中一种:我们视身体为我?灵魂为我?超然的我?与万物合一的我?我们的自我观是哪一种?或许我们永远无法体会统一意识,但我们会思考这种观念,并反问自己是甚么和甚么合一;我们可以观察是否身体内有灵魂,是否有「我」;我们可以观察身体与超然的自我,这种自我有甚么依据?我们错误的自我观是如此根深蒂固,所以当心是偏狭的,不是温顺、开阔的,根本无法观察实相。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这些错误的自我观只是支持自我存在的理念而已。
当我们不再需要或不再希望我执(ego assertion)继续存在,观察实相就容易多了。观察实相越清楚,就越容易禅修,因为我们知道「自我」是禅修的唯一障碍。「自我」只是一种观念,我们越了解这点,「自我」就越不会阻碍我们修行。
佛陀的教法不只是心理辅导之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去思考,继而以全新的方式去体验人生,这是为何佛教能绵延二千五百年而不消失的原因。心理学界不断有新的学说出现,而佛陀的教法是历久弥新,不可能有新的理论产生。当我们在修行时,我们应该试着去了解佛陀的教法,所以要有观察和思辨的能力。
在修止禅时,我们试着平静和专注;在修观禅时,我们如实的观察不同的现象,止禅和观禅应同时修习。从经典中我们知道佛陀的教法是完整的,我们不可以只选择一部份来修,而忽视其他的,这样是无法解脱的。所有修行的方法包括:持戒、守护诸根、知足、正念正知、修习止禅与观禅,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接着谈到第六禅:
复有比丘,超出所有空无边处,达「识是无边」之识无边处,因此先灭空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起「识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识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此段经文有关无色界定的解释非常简要,或许是布咤婆楼的程度还不够,或是有关的解释遗失了。
在第五禅,我们体验到空无边处,现在要做的是,将注意力由无边的空间转向观察空间的意识上。要观察无尽的空间必须有无尽的意识。从第六禅出定后,我们会自问:「我从中学到了甚么?」我们知道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整体(unity)。一旦接受了这点,统一意识便会生起。无论是在空无边处定或在识无边处定,我们都找不到有个人在入定,如果有,那就不是这两种定了,因为有个观察者在里头。在四禅,观察者缩到最小,这使心力大为提升,变得很清明。在第五和第六禅那,出定后,观察者充分了解,除了无尽的空间或意识外,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有了识无边处定的经历后,就会了解它是普遍意识(universal consciousness)的同义词,一旦我们知道:我们都属于普遍意识的一部份,就不会以任何不善的念头、语言或行为来污染普遍意识。我们都在普遍意识中,我们的意识越纯净,也越容易感受到纯净的普遍意识。在普遍意识里,有各种念头,无论我们想甚么、说甚么或做甚么,都在普遍意识里,而且不会消失。
我们将五禅、六禅来和初禅、二禅比较,当我们有快乐的感受,喜悦也会生起。我们要做的是将注意力从感受转向情绪,这些感受和情绪已经存在,我们只需觉知。从五禅到六禅也一样,只是比较微细。有了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会同时生起,我们只需把注意力从无尽的空间转到观察这空间的意识即可。
「识无边处」很容易被误解,特别是印度教把它视为修行上的成就,这种体验的确使人认为:「我就是那(I am that)」,梵文是tav tvam asi,也是用来形容统一意识。中世纪基督宗教神秘学家艾克哈(Eckhat)用了不同的术语:「上帝与我是同一的。」当时他几乎被处以火刑。我们猜测他可能进入高层次的禅那,除此以外,无法解释为何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他最大的努力(endeavor)不是想成为某个特定的人,很明显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傲,而是谦卑。
识无边处定是证悟和禅修的一部份,透过修行,当我们有了这种禅定,心也会越来越清明,越能观察实相,心不再偏狭,不再自我设限只关心特定的我。透过禅修,甚至可以超越「绝对自我」(absolute self)。从空无边处定和识无边处定出定后,我们会发现苦仍然存在,修行仍未结束;只要心中还有自我,这个自我必定有苦。所以观察我们所认同的是哪一种「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并自问:为何会有这种自我观。当我们发现这些自我观并没有根据时,我们的认知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第八章:七禅、八禅、九禅
-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灭尽定
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超出所有识无边处,达『所有皆无』之无所有处,因此先灭识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起无所有处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无所有处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想灭,此由于修习也。」这段有关七禅的描述和先前的一样简洁。英译者将无所有处译为no-thingness,这种翻译比较明确,让我们更能了解这个层次的禅那,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如何观察「无所有」(甚么都没有)。
第五、第六和第七禅经常被称为毗婆舍那禅(vipassana jhanas)或内观禅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色界的四个禅那证得内观智慧。
再扼要重述一遍:在初禅,心中已有我们想从外境追求的境界;在二禅,我们从禅定中所体会的喜悦是感官接触所无法产生的;在三禅,当我们无愿无求时,心自然会知足、平静。值得一再强调的是,要进入禅那,必须放下所有的感官欲望,包括放下想入定的愿望,若放下,便可以入定;在四禅,当自我变小时,寂止会生起,随之而来的是平静的心(even-mindedness)或舍心。
在五禅及六禅所生起的观智(insight),发现自我消失了,只剩下空间和意识。虽然有观察者,却找不到观察的「人」,因为观察者已经扩大到无尽的空间和意识。现在坐着正在读书的小小的观察者,根本无法体验到「无限」,而「无限」却可以在禅那中体会,观察者也可以扩大到无限。此时虽然有意识,这是心,没有「人」在那里。
在七禅,在无所有处,我们知道不但没有「人」,也找不到任何物体。同样的,在五禅(空无边处)和六禅(识无边处),没有任何物体可以执取,因为在整个宇宙中,根本没有可以执持的坚实物体。这些有关禅那的体验听起来很有趣,做起来是另一回事。有了禅那的体验后,我们有了内观智慧,因此对人和对世间的反应会改变,我们知道那些看似坚固的物体,事实上是不断变迁的。
七禅有两种不同的体验。我们可以觉知到非常微细的活动,一种粗略的比喻是:就像看着泉水不断流动一样。另一种体验是,我们觉知到广袤的空间,也就是无尽空间和无尽意识的合而为一,在这广袤的空间里,无一物可得。
要证得甚深的内观智慧并非一蹴可跻,要花时间,要一再证入不同境界的禅那,才能证得智(knowledge)与见(vision),才能应用自如,然而,这个境界不是涅盘,只是证入涅盘的过程。
布咤婆楼,比丘已达调御之想(controlled perception),彼由前至后,次第以达想之极致。
「调御之想」指禅修者在禅修时,首次能控制自己的心。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果真如此,我们决不会愚笨的让自己不快乐。「调御」意指我们可以想一些我们所选、所喜欢的去想,并放下那些对我们修行的目标和快乐无益的事。当心专注一境,进入禅那时,便知如何调御自己的心。很明显的,越高的禅那,调御的能力也越强,在三禅,禅修者的「调御之想」才真正开始。佛陀说:随着定力加深,我们一步步的迈向想之极致(limit of perception)。
「想之极致」是八禅的境界,使心能休息最久,使心充满精力,这是心进入第九禅那「灭受想定」(灭尽定)前的最后阶段,这就是布咤婆楼在第一章所问的「识最究竟的灭尽境界」。「增上想灭」的巴利文是abhi-sabba-nirodha。Abhi 意为「增上」;sabba是想(perception);nirodha是灭。经中记载,只有不还者(阿那含)和阿罗汉才能进入这种禅那。
某些论著详细描述九禅:进入灭尽定的人好像死了一样,因为呼吸如此微细,以致于难以觉察,然而仍有生命力,仍有体温及微弱的心跳。据说禅修者可以进入灭尽定达七日之久。通常,不需要入定这么久,故此举被认为是禅修者想展现其定力,这是佛陀反对的。
…处此想之极致时,彼作是念:「思虑(mental activity)之事,于我为恶;不思虑事,于我为善。」这里提到念头本身便是苦,这是很重要的内观智慧。任何心的活动-希望或欲望都是苦,因为有念头,心就会动,心动就会烦躁,烦躁会产生苦。,由于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因此苦也无法断除。例如,我们对过去的某些事情不满,希望有所改变,无谓的烦恼便随之生起。我们应该把「过去」放下,苦自然会消失。现在,我们正在修行,能利益我们的想法是去想如何解脱,而毋须去想过去的事。同样的,如果我们想着未来的事情,无论想得到某些东西,或希望某些事情不会发生,结果一样会产生苦。当我们真诚的面对自己时,就会发现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而这是那么愚痴!
「思虑之事,于我为恶;不思虑事,于我为善」并不是要我们像植物人一般没有思虑。佛陀拥有最敏锐的脑袋,以极高的智慧去解释人类的处境。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禅修以外的时间,有许多念头是多余的,这时候只要觉知呼吸、动作、景像和声音即可,不需要思考。透过禅那,我们学到如何注心一境,排除妄念,如果我们每天都这样修习,心就会更有力量,不会过劳。
设我仍有思虑意欲,我之想(perception)虽得消灭,而余粗想,将复再生。我今宁可不起思虑,不起意欲。
禅修者知道:在七禅及八禅所生起的隐约的「想」,会随着念头的生起而消失。与禅那的心境比较,平常的念头比较粗糙,尤其是不好的心境,如自我投射的作用,也就是把内心所想投射到他人身上,并责备所投射的对象。自我投射的人不会承认他人的坏处事实上是自己投射的。当然,在这个世间,我们必须有工作,必须交谈,这时的心是粗的,佛陀也不例外。在这部经中,佛陀以一般层次的心才能和布咤婆楼交谈,并回答他的问题。然而,我们要知道「想」虽有粗细之分,而微细的「想」会为心和生命带来优良的品质,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我们所想(we are what we think),所以我们要仔细观察自己的心念和选择所想的内容,越仔细观察,便越容易修习禅定。
彼于是不起思虑,不起意欲。不起思虑,不起意欲已,其想即灭,余想不生,而达于想灭。
Imagine可译为想象或幻想。由于巴利文是没有人说的语文(dead language),所以不容易翻译。当我们不起思虑,不起意欲,不再计画,不再反应、投射,那么比较粗的心便不会生起。世上一切的分别,包括喜欢与不喜欢,认为他人应该做或不应做,这些念头不再生起。只有当我们完全放下,禅那中比较微细的「想」才会生起。
佛陀接着说:
…而彼之想灭。布咤婆楼,如是次第而至增上想灭智定。
在这里,佛陀并没有详细解释八禅-非想非非想处(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此时,心处于没有活动的状态,观察(observing)几乎完全停止,但又不是完全没有觉知,所以不可以说有觉知,也不可以说没有觉知。在九禅(灭受想定),即使是三果(不还者)圣人,仍有些微「我」的感觉,尤如芳香之于花一般;只有阿罗汉的灭受想定完全没有「我」的感觉。
佛陀接着说:
布咤婆楼,汝曾闻如斯次第增上想灭智定否?
否也,世尊,吾今唯知世尊所说,谓:「布咤婆楼,比丘已达调御之想,彼由前至后,次第以达想之极致,处此想之极致时,彼作是念:思虑之事,于我为恶;不思虑事,于我为善。设我仍有思虑意欲,此想虽得消灭,而余粗想,将复再生。我今宁可不起思虑,不起意欲。彼于是不起思虑,不起意欲。不起思虑,不起意欲已,其想即灭,余想不生,而达于想灭。布咤婆楼,如是次第以达增上想灭智定。」「布咤婆楼,实如是也。」
布咤婆楼是个好学生,他记得佛陀所说的话。现在,他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了,他又有另一个问题:
世尊,世尊说示,想之极致(the summit of perception),为一为多耶?
佛陀答道:
布咤婆楼,吾所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
布咤婆楼接着问:
如是世尊,云何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耶?
佛陀回答说:
布咤婆楼,实如是如是达于想灭,如是如是现想之极致。布咤婆楼,故吾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
如果我们不用想(perception)灭,而用识(consciousness)灭,就比较容易了解佛陀的意思。在初禅,「识」有所转变,并非变得非常微细,而是有所不同。一旦出定,我们的识-想之极致便停止。随着定力加深,「识」变得越来越微细,直到我们达到最后的「想之极致」,也就是心的极限,接着进入灭尽定。佛陀的教导很有次第,他不但教我们最高层次的「想之极致」,也将每一阶段的顶点告诉我们。布咤婆楼仍不满意:
世尊,先有想生,而后智生耶?先有智生,而后想生耶?抑或智与想,非前非后而生耶?
佛陀回答:
布咤婆楼,先有想生,而后智生,实由想生,而智生起,故知:「实由此缘(conditioned)故,于吾生智慧。」在第六章我们讨论过心的四个层面:意识、感受、想和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因果关系,在智生起前,「想」必先生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有经验,智才会生起。不只修行如此,所有事情都是如此,例如,要了解无常,我们首先要观察呼吸或念头的生灭;要了解在禅那时的心识状态亦然,禅修者必须先有体验,然后才能「知道」所经历的过程。巴利经典将佛陀此处所说的「智」形容为省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有经验,之后才能省察。事实上,透过对经验的了解,内观智慧才会生起。我们都有开悟(enlightenment)的种子,如果对我们所体验到的事物没有真切的了解,就无法获得内观智慧,也无法开悟,这是佛陀的教导中很重要的部分。
佛陀接着说:
布咤婆楼,可知依此理趣,先生想,后生智,由想生,故智生起。
在这里佛陀直接回答布咤婆楼的问题。很明显布咤婆楼对此颇感与趣,却不熟悉禅那的境界,不然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他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世尊,想即人我耶?抑想与我(self)为异耶?
从相对的层次(世俗谛)来看,一定会有困难。人们视「想」为我。如果正在想的不是我,那么是谁在想呢?一定是「我」。我们的念头不停打转,就永远找不到答案;如果想要解脱,我们必须先放下所有的思想、观念。同样的,布咤婆楼也陷入世俗谛中,我们很容易认同他的看法,因为我们也有同样的观念。
佛陀想使布咤婆楼放弃「我」的错误知见,所以问布咤婆楼:「布咤婆楼,汝以何者为我?」布咤婆楼回答:
世尊,吾自思惟,粗我(gross self)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
布咤婆楼把身体视为我。佛陀回答说:
布咤婆楼,汝之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布咤婆楼,设若真实,则汝想与我,实非一物。布咤婆楼,由此差别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咤婆楼,如是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但于此人,犹有此想生,他想灭。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非一。
如果布咤婆楼的粗我(身体)是他的自我,那么他又如何说明「想」呢?想不断的生灭,如何可能和身体同一?布咤婆楼似乎承认这点,但又有另一个想法:自我是由意念所生。我们可能有同样的看法。人们经常说:「我不是身体。」这句话太突兀,比较有深度的看法是:「这个身体不属于我。」如果我们说:「我不是身体」,这暗示了拥有权,而谁是拥有者呢?当然是我啰。「我」拥有身体,「我」想保持身体健康,为它带来快乐的感官接触。身体属于我,正如屋子、车子、冰箱属于我的一样,这是布咤婆楼的看法:
世尊,吾以我为意所成(mind-made self),肢节具足,诸根圆满。
他仍不放弃「拥有权」的想法,只不过以「意」(mind)代替身体,「我是意所成」而不是「我是身体」。佛陀回答说:
布咤婆楼,汝之我为意所成,肢节具足,诸根圆满。布咤婆楼,设若真实,则汝之想与我,实非一物。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咤婆楼,若我为意所成,肢节具足,诸根圆满,然于此人,犹有此想生,他想灭。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非一。
布咤婆楼不得不面对真相,于是又想出另一个论点:「世尊,我以我为无形,而想所成。」事实上,布咤婆楼相当聪明。如果「自我」不是人的身体,又不是心,可能是某种无形无相的东面。「无形无相」(formless,无色)是佛陀叙述较高层次禅那的用语。佛陀再度告诉布咤婆楼:「想」是一回事,而「自我」是另一回事。假设有一个无形的自我存在,也不可能是想,因为「想」会不断生灭,所以想不可能是自我,佛陀试着让布咤婆楼了解这点。布咤婆楼又问道:
复次,世尊!人我(a person’self)即为想耶?抑想与我为异耶?斯义吾可得知否?
佛陀回答说:
布咤婆楼,人我与想为同一耶?抑想与我为异耶?汝欲知此,甚难甚难,以汝依他宗见,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学说为归,以他宗之行持为旨故。
佛陀的意思是,你不是我的学生,你向其他的老师学习,有不同的信仰,受不同的影响,所以要了解这些道理是非常难的。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相信有灵魂,相信往生后会快乐,或接受其他的修行方法,就很难了解。当然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经常如此,但要看有没有必要去改变。要了解佛法,我们一定要觉知自己的苦(这是第一步),最后我们会发现,以前的方法无法根除苦,或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彻底改变。
虽然后来布咤婆罗成了佛陀的弟子,但此时的他,仍满脑子的观念和理论,这些理论和观念是他从不同的老师听来的,或来自古代婆罗门的《梨俱吠陀》(Rg Veda),他们认为要透过记忆来修行,这些是布咤婆楼非常熟悉的。佛陀很温和的指出,布咤婆楼以前所学的障碍了他,使他无法了解佛陀的解说。结果布咤婆楼也放弃这些问题,不再提问,他们的对话到此告一段落。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布咤婆楼有完全不同的问题。此时,他是沉默的,很明显的,他无法理解自我的究竟实相(the absolute truth about the self)。
在本书的最后的一章提及不同时代所流行的不同的自我观,最后成为统一的自我(unity-self)。布咤婆楼的三个观点是:自我是身体,是心,或是无形的。他不了解所有的自我观只是概念而已。同样的,我们也有自己的见解,因为这些见解是「我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见解。想想看,这些见解是否有稳固的理论基础?只因为「我」有对某人或某些事物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否真实不虚?当然,在绝对的层次,这些都是不实在的,因为一切事物都会变动、消失。即使在相对的层面也无法保证这些都是真实的。
我们应该经常检视自己的想法,看看这些想法的来源。如果这些想法是负面的,就要知道这些想法的源头,为甚么会有这种观念,其实所有的观念都源自内心,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心的投射(projection),甚至自我的观念也是一种投射。当我们希望某个想法能实现时,是因为这种想法能满足我们的贪欲。如果我们知道贪欲无法带来喜悦,那么我们会比布咤婆楼懂得更多,我们会观察过去信以为真的观念,所有的现象都不断的在生灭,所以没有永恒不变的「我」。
如果没有我,那么是谁指示身体去打坐,我们真的相信有个我在操控一切,就如演木偶戏的人操纵木偶一般。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就需要一再的探讨这种观念是否成立。
和布咤婆楼一样,我们也受到不同的影响,我们被其他人的思想所影响,被我们的经验和信念所影响。佛陀提供我们修行的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略尝解脱之味。没有「自我」使我们能够解脱,能够去除贪与嗔。佛陀向我们宣说他所体验到的、所证悟的法,我们只要依教奉行,便可究竟解脱。
第九章
出离、离欲和四圣谛
此时,布咤婆楼又开始一系列新的问题。我们都是这样的,如果无法了解某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会转换话题。
世尊,「此想为人我耶?抑我与想为异耶?」甚难知之。如是世尊,复欲请问: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佛陀回答道:
布咤婆楼,「世界常住(eternal)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此为吾所不记。
佛陀和布咤婆楼接下来的问答如下:
世尊,世界非常住耶?
「世界非常住耶?」此为吾所不记。
复次世尊,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如是世尊,世界无限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这种现在看来非常麻烦的四段发问法,当时在印度非常流行:「是如此?非如此?既是如此亦非如此?既非如此亦非不如此?」布咤婆楼用这种问法问了十个被佛陀称为「无记」(the Undeclared or Indeterminate Points)的问题。佛陀不回答,也不去讨论这些问题。学者们认为:当时的苦行者、游方僧和宗教领袖常用这些问题来表明各自的立场。佛陀和布咤婆楼的对话继续:
复次世尊,此命与身为一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如是世尊,如来死后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如是世尊,如来死后亦存在亦不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如是世尊,如来死后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最后布咤婆楼问道:
世尊,凡此等等,世尊何故判为不记耶?
佛陀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布咤婆楼,此不与义合,不与法(Dhamma)合,非梵行,非趣出离,非趣离欲,非趣止灭,非趣寂静,非趣证悟,非趣正觉,非趣涅盘,是故吾判为不记。
这些问题对修行无益,对法无益,对灭苦也毫无帮助,不会使人出离、离欲、证悟和涅盘,所以佛陀把它们判为「无记」,不以讨论。
对布咤婆楼来说,世界是否恒常对他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而灵魂与身体是否同一,又怎会影响他的幸福?至于佛陀死后是否存在和布咤婆楼有甚么关系?这些问题无法使布咤婆楼解脱苦,所以佛陀拒绝作答。
在其他经典也有类似的讨论。例如,有个叫婆蹉衢多(Vacchagotta)的外道曾问佛陀:如来死后是否存在?是否既不存在也非不存在?或既存在也不存在?佛陀说他不会讨论这些问题。婆蹉衢多说他不了解,于是佛陀叫他去收集木柴,用木柴起火,接着叫他多丢一些木柴到火里,并问他火势变得如何。婆蹉衢多回答说:火势很猛烈。之后佛陀叫他不要再丢树技到火里。一会儿,佛陀再问他火势如何,他回答说火势弱了,不久便熄灭了。佛陀告诉婆蹉衢多说:如来死后也一样会熄灭,并问他:「火焰往前方、后方、左方还是右方?」婆蹉衢多回答说:「火焰并没有往哪里去,而是熄灭了。」佛陀坚持问他说:「火焰究竟往上还是往下?」婆蹉衢多回答说「火熄了,因为没有燃料。」佛陀回答说:「如来也一样,死后会熄灭,因为不再有欲望的燃料。」今天,人们以不同的文字来问同样的问题。即使在佛教国家内,对佛陀死后是否存在也有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佛陀说得很清楚:只要欲望之火不再有燃料,则身心都会止息。我们毋须再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或在心中和自己争论。
佛陀告诉布咤婆楼,他不会回答一些对修行无益,对「法」无益的问题。在《箭喻经》中,佛陀以很好的比喻来说明这点。假设有个人被箭射中胸部,并在死亡边缘挣扎,却不让医生为他治疗,坚持要先知道箭柄由何种木材制成,箭尖用的是何种毒素,箭尾的羽毛是鹅毛还是鹰毛,箭头是甚么东西做的,还有是谁射的箭,在哪个距离射的,为甚么要射他?当然,等找到答案时,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反映人们习于询问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去修习可以解脱苦的方法。在经中,箭代表苦,佛陀是医生,治疗代表法(Dhamma),那个中箭的人是拒绝接受佛法的人,除非有人先把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告诉他。
佛陀对布咤婆楼说一样的话,佛陀说布咤婆楼的问题和修行无关,而布咤婆楼也只是问问罢了,他纯粹是被佛陀所吸引,所以才花许多时间和佛陀讨论。佛陀也认为布咤婆楼是孺子可教,否则不会花大半天和布咤婆楼讨论。我们也非常幸运,如果没有布咤婆楼的问题,佛陀就不会如此详尽的解释。
佛陀说:回答这些问题不会使人出离,离欲,不会使人寂灭、寂止、证悟和涅盘。「出离」是趋向开悟的重要一步,被称为出世间的缘起,也就是觉察到自己的苦,并对佛法生起信心,同时也对自己能够修行感到喜悦。接下来是禅修,也就是正定。禅修会带来「如实知见」,也就是证得内观智慧-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无常、苦、没有实体的智慧。「如实知见」可以使人出离世间,出离是解脱苦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所有的修行只是准备而已。我们无法全心投入修行,是因为心仍然向外攀缘,认为只要找到意中人,找到合意的工作或理想的住所,就可以去除烦恼,认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在这世间生活,为了生存,我们需要氧气、阳光、雨水、食物和其他的东西;而内心的满足是无法依靠外境的,我们不可能由外境获得满足,真正的满足来自内心。要了解这个真理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有些人快些,有些人慢些,而有人永远无法了解,这要视各人的业果和机会而定,当然,机会也就是业果(karmic resultants)。
出离并非指我们讨厌这个世界、世人、大自然或其他事物。出离不等于厌恶,虽然有时出离被译为厌恶。「厌恶」有负面的含意,而负面的心态会破坏修行。我们不是厌恶这个世间,而是不再执着外在的事物,不再认为这些事物能为身心带来快乐,因此不会在世上追求绝对的满足。年轻人很少能出离,当然也有例外。大部份的人都要在一再的失望后,才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追求幸福。
禅修的人不一定能体验到出离,因为许多人只是想为生活添加乐趣才来禅修。佛陀说这比不禅修要好。佛陀很乐意为人解答问题,在《布咤婆楼经》中,我们发现佛陀非常直接和简明的回答布咤婆楼的问题:不要想外在的东西,想想如何出离。如果我们禅修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命中较高的层次,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会做到。
透过禅那,我们发现有不同层次的心识状态,即使是凡夫俗子也能做到。此时,我们会发现这世间给我们的只是假的黄金而已,虽然闪闪发光,却毫无价值。美丽的女子,英俊的男子,宜人的天气,可口的食物,醉人的音乐,极佳的书本,这一切只是感官接触而已,都是外在的,无法触及内心深处。巴利文称这些东西为诱惑(mara,魔罗)。我们不断的被外境诱惑,并非因为外境多么诱人,而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幸福可以从外境获得。有些人表面上看来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我们会想:「为甚么他们可以尽情享受人生,而我却不能?或许照着他们所做的去做也会一样快乐?」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去做,就会失去追求解脱的机会。要做到出离,需要长期精进的修行,即使做到了,也只是踏出深入了解「法」的第一步而已。
出离之后是离欲,离欲是证入涅盘的起点。修行到了这个阶段,出离心会非常强,一旦贪或嗔生起,我们会立刻去除贪与嗔,然而贪与嗔并非真的消失,只有在证悟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三果阿那含),贪与嗔才会完全消失。即使如此,它们仍会若隐若现,但完全不会干扰我们;只有阿罗汉-开悟的人才完全没有贪与嗔。离欲使我们不再执取、执着或是排斥反抗,虽然随眠烦恼仍在内心深处,但我们能把它放下,因为我们了解出离的真理,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我们的修行之旅。
出离和离欲是修行道上重要的阶段,首先必须知道自己的苦。偶尔禅修是不可能出离和离欲的。知道自己的苦,并非指我们必须遭遇某种重大的悲剧。苦是心中的不安、焦虑和忧虑;有了苦,便无法安心。一旦体会到苦,对佛法的信心便会生起。这时我们才会认真修行,去验证佛陀所说的法,而不是盲目的相信佛陀的话。投入修行会有法喜,这种喜悦远超过世俗的感官之乐,而这种喜悦使禅修成为可能,这是出世间缘起的因果关系。下一步是安止定,接着是如实知见,也就是如实的了解一切现象都是无常、不圆满(苦)和无我的。
经历了一件事并不表示我们必定了解这经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很少的知识便可以过生活,正如阅报一样,只需少量的词汇就可以明白大概。我们的日常生活不需要高深的智慧,只要我们能够处理日常事务即可;而遵循佛陀的教导,我们必须更深入,必须觉知当下所发生的事和每个念头的生灭。
如果我们照着做,就会发现:无常是生活的一部份,这比起表面接受「一切都是无常的」或「吸呼是无常的」要深入得多,我们深深了解无常是与我们有关的真理。我们也以同样的方法去体会苦,我们一再的体会到苦,知道内心深处的不安,知道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去追求外在的事物。我们责备他人,认为自己的苦是他人造成的,忘了别人和自己一样,内心也一样不安,我们找一些理由来解释内心的不安,这些表面的原因只解释表面的经验,无法说明内心深处的烦恼,因此无法根除苦。
觉知到无常和苦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在自己身上看到无常和苦,也要在每一件事物中看到无常。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每一根草都在宣说无常的真理。每天都充满无常,我们可以从有数字显示的时钟上看到每一秒都在变动,无常就显现在时钟上,然而我们总是认为:虽然时钟的数字在变动,而我们是静止的,这怎么可能?我们的身体和数字钟一样,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离欲对我们的生命有重大的影响,一切事物都有其因果,透过修行才能离欲。有时我们舍弃了某种欲望,我们以为已经离欲,所以当其他的欲望生起时,我们会感到讶异。当然能够舍弃欲望是值得称赞的,也非常重要,但不表示已经完全离欲,因为我们仍有欲望,所以仍要修行。在婆蹉衢多的故事中提到,当所有的燃料都耗尽时,火焰才会熄灭。有些人会说:「但我喜欢欲望。」如果我们如此认为,那么只好等待,等到有所改变,或许是今生,或是来生,或是一百世以后,谁知道呢?或许是明天也说不定。对生命的态度改变,心才会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也会大不相同。
禅修得越好,心会变得越清明,越能看清生命的真相。大部份的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他们希望世界如同他们所想的一般,然而现实生活与想象并不相同,所以许多人不快乐。我们也不会安于现实,如果会的话,那么所有的富人都会感到满足,就不会有富人绝望的自杀。或许我们知道这些事,但我们有没有对治的方法呢?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做的有一大段距离。重要的是,如果真的知道要怎么做,就要赶快去做,否则不会进步,因为知识无法带来改变。
佛陀在《布咤婆楼经》中说道:离欲可以导致止灭、平静和证悟。如果心中有贪与嗔,是无法超越自己的,因为心被贪、嗔所困。当我们的念头不停打转时,我们最能感受到这点。和布咤婆楼一样,我们的心充满各种想法和见解。只要心中有贪与嗔,我们就永远无法平静,也无法体验到高超的意识境界。
在禅修时,如果心能平静下来,就会了解这个世间只是为身体提供必要的东西,外在的事物无法带给我们幸福快乐,所以不要太重视。当然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事,我们仍需注意,而在禅修时,我们应断除贪与嗔,做到这点,才能达到更高的禅那和证悟。巴利文abhibba意指证智,也就是去除五盖和随眠烦恼,禅修到了这个境界,贪与嗔都会消失,不再障碍我们。
佛陀通常以四种方式回答问题:直接回答「是」或「不是」,有时会详细解释或反问,最后是以沉默作答。在《布咤婆楼经》中,佛陀对布咤婆楼说讨论这些问题对修行无益。接着布咤婆楼问佛陀:作为导师的佛陀会讨论那些问题:
如是世尊,世尊所记为何?
佛陀回答:
布咤婆楼,「此是苦」为吾所记,「此是苦因」为吾所记,「此是苦灭」为吾所记,「此是灭苦之道」为吾所记。
这是四圣谛,是佛法的精髓。布咤婆楼之前的问题太不切实际,佛陀把他拉回最基本的实相。四圣谛是佛陀证悟后所宣说的法,佛陀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证悟后,入定七天,出定后,他有系统的宣说四圣谛,帮助人类脱离困境。在开悟后,佛陀对以前的同修五比丘所开示的第一部经是《转法轮经》,其中一位听后立刻证果;之后,其他四位比丘也证果了。他们是第一批僧伽,是佛陀最初的弟子。
灭苦的方法是八正道,八正道可分为戒、定、慧三学,本书都提到了。布咤婆楼听过有关持戒的必要,也听过禅那即「定」的开示。当讨论「自我」是否存在时,他已经初步接触到「慧」。很明显的,布咤婆楼到目前为止还认为「自我」是存在的,他将继续问有关的问题,直到他成为佛弟子时,他才相信「无我」。
佛陀的教法永远包含戒、定、慧三学,无论少了哪部份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值得遵循的修行法必定包括戒、定、慧三学。我们也把「定」称为三摩地(samadhi),或译为平静、宁静、寂止。平静的心才能生起智慧。
布咤婆楼仍有问题:
世尊所记,为何故耶?
佛陀很有耐心的回答:
布咤婆楼,此合义合法,是根本梵行,趣向出离、离欲、止灭、寂静、证悟、正觉、涅盘,故为吾所记。
此时此刻,布咤婆楼终于明白:
诚然世尊,诚然善逝。世尊请便,今正是时。
于是世尊起座而去。
布咤婆楼得到的启示非常重要,只有问「对修行有益的问题」才有用。那时在印度或现在,那些婆罗门、僧侣、精神导师喜欢长篇大论的讨论世界是否永恒,是否无限,灵魂与身体是否相同等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对修行无益,只会造成更多的空想,对修定没有益处。
最有益于修行的问题是深入了解四圣谛,并在心中好好体验。第一及第二圣谛是「苦」及「导致苦的原因」-也就是贪欲,执取与嗔心,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体验得到。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两种圣谛,就能了解第三种圣谛:苦的止灭(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第四种圣谛:灭苦之道(道谛),也就是八正道可以导致解脱。问这些问题才有意义,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直到完全了解。我们自问:「我有苦吗?如果有,是否把这些苦归于外境?是否认为是外境或某人使我受苦?或认为苦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必须一再的问自己:「是谁使我受苦?」在理智上,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没有人有兴趣使我受苦,没有人会这么做。」无论是如何合理的解说都没有用处。我们必须了解苦是源于内心的贪欲、嗔恨和执着,一旦我们放下所有的欲望,苦会立刻消失。
有些欲望看起来是好的,例如,我们想有一节好的禅修,一旦我们这样想,还能静下来禅修吗?当然不能!根本无法入定。如果有「我想要」的念头,就会有苦;假如我们放下「我想要」的念头,坐下来,盘起腿,把心安住在当下,没有任何欲望,我们会发现真的很有效,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即使我们的心仍妄念不断,只要放下欲望几秒钟,就会感到非常轻松。此时,我们放下重担,就像放下沉重的包袱。当然,未受训练的心会立刻重拾包袱,只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放下,我们不但能熟练的放下贪欲,也能看到修行的成果:心量扩大、开阔、自在、轻安、平静。
如果我们能全心投入禅修,又没有任何期望的话,效果会更好。我们也会变得明智,知道要放下佛陀所说的纯属推测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修行没有帮助。布咤婆楼很喜欢问这类问题,布咤婆楼所问的问题使我们了解甚么是对修行有益的,甚么是无益的。
第十章
贪爱的止息:趣向涅盘
在前一章,布咤婆楼对佛陀说:「诚然世尊。」而在佛陀离开辩论堂后,那些外道转向布咤婆楼:
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皆向布咤婆楼作讥诮言:「布咤婆楼,汝于沙门瞿昙(Gotama)所说,作如是赞叹:诚然世尊,诚然善逝。然于世间常住耶,世界为无常耶,世界有限耶,世界无限耶,命与身为一耶,命与身各异耶,如来死后存在耶,如来死后不存在耶,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等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布咤婆楼闻是言已,告彼等苦行外道曰:「诸君,世间常住耶,乃至如来死后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固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然沙门瞿昙所说之道,如实真正,如法合法。
那时佛陀已经很有名了,外道们仍以「沙门瞿昙」来称呼佛陀:而不是以觉者(Buddha)来称呼,这意味着他们认为佛陀只是他们的一份子。另外,布咤婆楼用了「法」(Dhamma)这个字,现在我们用来指佛法(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那时,布咤婆楼不是佛陀的弟子,这是他第一次听闻佛法,这表示当时常用「法」字来指绝对的真理、自然的法则。布咤婆楼继续说道:
理智如吾者,何不赞叹此善说法者耶?
虽然布咤婆楼不是佛陀的弟子,他发现佛陀的教法非常珍贵,合理。经文继续:
后二三日,象首舍利弗与布咤婆楼诣世尊所,象首舍利弗礼敬世尊,坐于一面,布咤婆楼亦亲礼世尊,殷勤问讯已,就一面坐。
我们假设象首舍利弗曾经听过法,是佛陀的信徒,布咤婆楼只和佛陀互相问讯,然后告诉佛陀他离去后,那些外道嘲笑他的事。佛陀说:
布咤婆楼,彼等苦行外道皆悉盲目,为无眼子,唯汝一人,具眼士也。
佛陀经常用「眼中只有微尘」来形容那些容易了解佛法的人,事实上,佛陀在证悟后,坐在菩提树下享受涅盘之乐时,并不想去教化众生,因为他的教法与众生所听到的大不相同,所以众生不会了解他证悟的法。最后,梵天(Brahma)向佛陀请法,请佛陀为了天人与人类的福祉,一定要弘扬佛法。然后,佛陀观察众生,发现那些「眼中只有微尘」的人,为了他们,佛陀决定成为他们的导师。佛陀继续说:
布咤婆楼,我所说法,有决定记,不决定记。布咤婆楼,云何名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
佛陀再度说明哪些是「无记」的问题,即:世界常住或不常住,世界有限或无限,命与身为一或各异,如来死后存在或不存在,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等问题。
布咤婆楼,以此等不与义合,不与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离,乃至非趣涅盘,是为不决定记(无记)。
佛陀再度强调,他只说趣向究竟解脱的法,所以无论佛陀教的是何种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究竟解脱。可惜无论是佛陀时代或者是现代,有许多导师都不了解这点。
今天,同样的,修行的旅程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趣向涅盘,而不是灭去(annihilation)。涅盘没有这类东西,只有清明、圆满和完全的觉知,以及无明的止息。这种觉知不是全知,佛陀说他无法同时知道所有的事,但只要佛陀去思考,就能知道任何事。虽然「全知」令人刮目相看,却不是证入涅盘的目的,涅盘是无明的止息,苦的止息。
布咤婆楼,云何为我说法之决定记?亦即此是苦,此是苦因,此是苦灭,此是灭苦的方法。…以此等与义合,与法合,是根本梵行,是趣出离,离欲,止息,平静,证悟和涅盘,是故此等为我说法之决定记。
佛陀把布咤婆楼带回四圣谛,向他说明如何一步一步的修习内观,趣向涅盘,直到所有的无明消失。
我们已经知道出离和离欲了,接下来是止息(cessation)。止息指想、受的止息,指在九禅进入灭尽定或灭受想定。止息也指苦的止息,如佛陀所说的,止息指三种贪爱不再生起。这三种贪爱是:「欲爱」,指渴求感官欲望的满足;「有爱」,指渴望生命的存在;以及「无有爱」,指渴望生命不存在。这三种贪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主要原因。我们或许会责怪父母,让我们学了许多坏习惯和给我们许多坏的影响,父母亲可能会做出许多没有智慧的事,因为他们尚未开悟,我们不应该责怪父母,是我们的贪爱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到特定的家庭,所以我们应该观察自己的贪爱。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渴望感官欲望满足的「欲爱」,如果我们能自我观察,可以看到心中的「欲爱」。而渴望生存的「有爱」就深入得多,「有爱」是我们最强烈的欲望,是使我们生死轮回的主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觉察到「有爱」。人们经常使自己忙得团团转,去避开看到不如意的事,这是人们对治苦的方法。如果我们深入观察「有爱」,就会了解佛陀的教导,因为渴望生命存在的「有爱」会导致持续的苦。
「有爱」使我们去找些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心,这是为甚么我们会不停的想,不断的动,以及去避开不如意的事。想想看我们早上的床是甚么样子,乱成一团,为甚么?因为即使在睡觉,心仍不得安宁,仍有苦受,所以身体会动来动去。我们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甚么?我们会不会想:「啊!活着真好!」会这样想的人非常少。大部份人会想:「又来了!」或是类似的话。有多少人能觉知醒来时的念头?意识是如何生起的?念头是如何生起的?我们如何造成这一切?我们告诉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很无聊。其实这些只是在支持一种假象:自我。这个自我很忙碌,因为忙碌表示自我很重要。这个假象满足了「有爱」,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朝向这个目标-有爱。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自己,我们会发现果然如此,即使是动机最善良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有爱。
仔细审视一天的生活对修行很有帮助。审视今天的生活,由于时间太近,可能有点难。我们可以想想昨天是如何过的,做了甚么事?想些甚么?如何保持自我这假象?我能够观察到不断生灭的身心现象中的「有爱」吗?身心不断的变动,我们的心想东想西,想将来可以做些甚么,想过去做了甚么。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想,才知道自己的存在。所有的心理活动只为一个目的:满足「有爱」。
禅修时,只有一个禅修对象-如观呼吸,就可以使我们去除妄想。禅修时,如果我们能去除妄想;禅修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去除妄想;去除妄想后,心就会平静、宁静。
「无有爱」(the craving for non-existence)只是硬币的另一面,源于同一种假象-即有「我」的存在。不过此处的「我」并不想存在,可能是生活中有些事情非常糟,使「我」想逃之夭夭,也就是渴望不存在。「有爱」因为渴望存在,所以会障碍我们体证涅盘。如果我们了解苦,也愿意审视「有爱」,那么要小心不要堕入「无有爱」的陷阱,如果我们觉得人生充满苦,因此想逃避,这也是一种贪爱,因为是我想要「去除」某种事物,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放下所有造成「自我」假象的事物,要一再的、如实的观察身心的变化,而不是如我们所想的一般。假如我们有太多的成见,就不会进步,就像嘲笑布咤婆楼的外道一样,他们不想听任何新的理论。布咤婆楼则不然,但到目前为止,他仍不得要领。
观察这三种贪爱非常重要的,要深入观察,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在禅修时、坐在树下或走路时都可以。
接下来佛陀要说的是平静,我们要学习去除妄念,这些妄想使心无法平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必要的思考,我们有念头,是因为要让心忙碌,要观察这点并不难,我们可以用修行来去除妄念,此时只有觉知,心是清净的,好像透明一般,心是平静的,这种内心的平静有助于恢复精力。我们的念头使我们疲累,我们的工作或许只需少量的体力,或许只是按按键盘或挥动笔杆,但一天下来却疲惫不堪,这是因为心不断的思考、盘算和反应。当没有必要时,我们是可以不去想的。
要做到以上所说的并不容易。只有当「有爱」止息,纯然的觉知才会生起。在止息贪爱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含意,我们必须观察贪爱不断生起,以及永远无法满足,贪爱会使我们不安和焦虑,这些在外表是看不到的。我们的内心经常不安,我们使这种不安合理化,并归罪于外在因素,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爱」。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有恍然大悟的经验。禅修进入状况时,会有平静的心,而平静的心比较客观,也更容易观察到心中的贪爱。通常我们会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虽然会花许多时间,但如果我不去做,谁会去做呢?」有许多类似的念头会生起。
如果只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和表现,我们会发现都是内心在推动的,这些都是「有爱」的表现;那么修行的动力是不是呢?这是一种矛盾,我们需要修行的动力,去观察和了解佛法也需要动力,而为了证入涅盘又要将这动力放下。从需要动力和放下动力,就好像转换轨道一样。当我们深入观察自己时,我们会知道心中所有的念头,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我们毋须厌恶、责备或怨恨自己,也不会有罪恶感,心中所有的念头都是人性的一部份,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生起的原因,然后超越它。观察「有爱」是非常有趣的修行,虽然有点难,但能带来重大的成果;而容易做的事,通常不会有大的成就。
心止息和平静后,佛陀提到下一个阶段:证悟。证悟有不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指我们知道已经去除五盖以及和五盖有关的随眠烦恼。只有断除有爱才能去除五盖。在清净道上修行,我们不断的减轻五盖的影响;而支持我们修行下去的就是禅修、正念。此时,我们仍不能根除五盖,因为仍有贪爱和嗔心,直到修行的最后阶段才能彻底断除贪与嗔。随着证悟而来的是涅盘,涅盘是修行之旅的终点。
透过禅修和净化内心可以体证涅盘。观察内心深处的贪爱-贪求生命的存在,可以知道贪爱是使我们去做最愚蠢和可怕的事的关键,使我们从早到晚去做那些我们经常做的事。
现在,佛陀再度向布咤婆楼讲述内观智慧之道,这条道路通往涅盘和四圣谛。佛陀知道布咤婆楼仍无法领会,所以佛陀用其他的词句来说明:
布咤婆楼,或有一类沙门婆罗门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这是熟悉的天堂的观念,有天人在弹奏竖琴和永远幸福快乐的地方。现在,在某些佛教圈子仍非常流行这种观念,例如,借着念诵佛陀的名号,希望能往生净土,永享快乐。
我访彼等,如是问曰:「诸友,汝等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真实否耶?」彼等闻是言,报我曰:「然」。
我又问曰:「诸友,一向安乐之世界,汝等实知实见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否也。」我又问曰:「诸友,汝于一夜或一日,于半夜或半日,亦曾审知有一向安乐之我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否也。」佛陀不但告诉布咤婆楼那些婆罗门所宣扬的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而且指出如果想在这个世间找到快乐,等于走上歧路。很明显的佛陀要布咤婆楼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建议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拿这一天来反省,用刚才观察「有爱」的方法,观察我们如何周旋在不同的事情中?我们做了一件事后,由于不满意,又去做另一件事,正如佛陀所说的:「你们曾于一夜或一日中,感到完全快乐吗?」这并非指我们必定不快乐,虽然有时我们的确不快乐。如果我们回想平常的日子,会发现甚么?发现对生活不会十分满意,或许有片刻的欢乐,但能持续多久?而那些情绪和念头无法带来平静或涅盘;这些情绪和念头又不断生起,这就是苦,这种苦是因为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是无法摆脱我们不想要的事物。我们应该尽可能仔细观察这种苦。
我们并非对生命厌倦,如果我们正确的观察,反而更容易接受生命中不圆满的现象,既然佛陀已经找到解决方法,我们便应跟随他的脚步,亲自去验证佛陀所说的法。去观察心中的不满可以减轻苦,因为我们可以接受生命本来就是如此。而一般人对苦的反应是感到痛苦和哀伤,这是无济于事的,当我们受苦时,我们无法如实观察事物。所以观察「这一整天,心起了甚么念头」是很有帮助的。生存是为了甚么?
佛陀接着问那些婆罗门和苦行者:
「诸友,趋于一向安乐世界,惟此道可实现,惟此路得通达,汝等曾了知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否也。」今天,我们可以在许多叙述神秘经验的杂志上找到这些理论和观念-宣称能获得安乐的方法,很明显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仍有「有爱」,一定还有苦。尤其是在「有爱」的背后隐藏着对不存在或断灭的恐惧,显现在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有人会说:「我不怕死。」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是很容易面对的,他们会说:「只要不受苦就好。」或「只要比我心爱的人先死就好了。」而对死亡的恐惧是非常真实的苦,隐藏在「有爱」中。
当我们觉得被忽视,不被接受或没有人爱时,也会有断灭的恐惧。为了得到别人的欣赏,有些人会用尽一切方法,这样的生命非常不圆满,因为要仰赖别人的意见和情绪,这是非常不可靠的。
当我们认为自己很特别和与众不同时,就需要一些东西来支持;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时,就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虽然有时我们会得到我们渴望的爱与赞赏,而长远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得到赞赏。因为自我是建立在假象(illusion)上的,需要不断的支持。自我的假象越深重,所生起的贪爱就越危险。正如一个很肥胖的人想走过一道很窄的门一样,一定会撞到门的两侧。
同样的,如果我们去保护「自我」,那么即使是些微的批评或不谅解也能伤害「自我」。自我越大,越容易受伤,反之则越小。如果没有自我,就根本不会受伤。如何缩小自我?去观察,每分每秒的观察我们的「有爱」,内观智慧就会增长。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苦,却不知道如何离苦,我们以为修行是唯一可以减轻苦的方法,我们透过去做,去说,去体验某些事,希望能带来快乐。佛陀离苦的方法不是这样,佛陀说如果要真的快乐,唯一的方法是去除「自我」这个假象,亦即完全去除「有爱」。佛陀继续说:
我又问曰:「诸友,生彼一向安乐世界之天神曰:『尊主,若欲实现一向安乐世界,当行善业,当步正道,所以者何?吾等所行正尔,故得生于一向安乐世界?』汝等曾闻其说示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否也。」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合正理否?
对于一些错误的观念,佛陀会指出这种观念是愚痴的,佛陀不认同一些无法探讨问题核心的修行指导,《布咤婆楼经》不是唯一记载佛陀批评外道的理论是愚痴的,特别是当他们误导他人时。此时,佛陀举了一个比喻:
譬如有人作如是言:「吾于此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余人若问曰:「吾友,汝于此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则汝当知,国中所谓第一美女,属剎帝利族耶?婆罗门族耶?吠舍族耶?抑首陀罗族耶?」彼闻是言,答曰:「不知。」又问彼曰:「吾友,汝于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名何姓何?彼女身躯长耶短耶,抑适中耶?彼女皮肤靑黑耶?黄金色耶?彼女所住,为村落乡镇抑城市耶?」彼闻是问,答曰:「不知。」又问彼曰:「吾友,汝所求交且爱者,汝不知其人,不见其人耶?」彼闻是问,答曰:「唯然。」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否?
布咤婆楼回答:
世尊,此人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布咤婆楼似乎对佛陀更有信心,因为现在他称佛陀为「世尊」。佛陀继续说道:
布咤婆楼,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合正理否?
世尊,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佛陀想让布咤婆楼知道,这些导师并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信仰,他们非常愚痴,就像想找国内最美的女子的人一样愚痴,因为他不知道最美的女子是谁,住在那里。
许多宗教都相信有一个永远快乐的世界,如果我们过着正当的生活,没有犯许多罪,死后这个「自我」就会永远幸福。佛陀从来不认同这种理论;相反的,佛陀说:通往快乐的唯一道路是观察「自我」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心想出来的(mental formation)。佛陀举了另一个譬喻:
例如有人,于四衢道处,欲树立一梯,以登殿堂。有人问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东方,西方,北方,抑南方耶?此殿堂高耶低耶,抑适中耶?君知之乎?」彼于此问,答曰:「不知。」此人又问:「吾友,汝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君不知亦不见耶?」彼于此问,答曰:「唯然。」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否?
世尊,此人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换句话说,有人想去梦想中的快乐天堂,却不知在哪里,或是如何去。佛陀花了不少时间来说明这点,佛陀想指出布咤婆楼的错误观念,尤其是有关自我的理论,只是这次佛陀以不同的主题来说明,佛陀对布咤婆楼有无限的耐心,以不同的方法来解说「法」,希望布咤婆楼能够了解。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布咤婆楼,因为要了解「自我」为何物并不容易。这个「自我」坐在这里,想得到快乐,却不知道「自我」本身会妨碍快乐,妨碍知足和满意(fulfillment)。
如果我们主观的看自己,可能会看到「自我」,如果我们客观的观察,就会发现「自我」只是一种观念,是心理作用而已。禅修的人都知道,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但至少我们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知道是甚么引起内心的忧喜烦躁与不安。为甚么我们不断的渴求和排斥某些事物,这是渴望生存的「自我」假象所造成的。当我们越了解实相,就越能感到佛陀的伟大,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佛陀首次将人类的处境和超越的意识,如此明确的勾划出来。
许多人皈依佛陀,向佛陀祈祷,却不知佛陀伟大之处。如果在今生今世能了解佛陀的伟大之处,表示我们有相当好的业果,这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去了解佛法,去探讨生命的本质,指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现实相、真理,我们往内心观察,如果我们观察自己的心就能了知法,这并非指我们要去除「自我」,而是要了解自我只是一种假象,如果不了解,就永远放不下。深入了解法,了解生命的实相,是放下的先决条件。
第十一章:灭除自我的假象
以前布咤婆楼在界定「自我」时碰到很大的困难:
布咤婆楼,有三种我得(acquired self),即粗我得(gross self),意所成我得(mind-made self),无形我得(formless self)。
我们会误解acquired这个字。如果用另一个字assumed(假设的),自我就会更清楚,指这个「自我」是假设的。
何者是粗我得?粗我得有形,由四大所成,段食所养者,粗我得也。
很明显的这是指身体。身体和欲界(kama-loka)有关,Kama是欲望,loka是地方或处所的意思。欲界是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有种种的欲望,欲望是我们的一部份,也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要超越欲望必须很努力,要知道欲望所带来的苦,虽然我们仍在相同的世界里,最后我们仍可以达到没有欲望的境界。
和布咤婆楼一样,我们以为「粗我得」是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很矛盾的感情:当身体疼痛、生病或不听话,我们就会很讨厌;当身体健康,有许多快乐的感官接触,我们会觉得「有」身体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不认为身体就是我,而认为我们拥有身体,把自己当成某个人,也就是把身体当成自己,没有发现身体也是一种自我的假象。
佛陀告诉我们:身体的欲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佛陀说:身体有各种感官欲望,我们应该观察这个身体,观察「身体」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对象,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拥有身体」的观念与事实不符。没有人想让身体生病,受伤,老化和长得丑,没有人要让身体死去,可是身体却有这些事,如果我们真的拥有身体,为什么身体会这样?
身体由四种元素构成,即地、水、火、风。这四大种又称为色(materiality,物质),由食物所养。身体有许多欲望,如果没有欲望,生活会简单多了,我们不需要厕所、浴室、淋浴,也不需要厨房;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买东西,去种植蔬果,去准备食物来养活这个身体。
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家里有哪些东西?一切都为身体而设:厨房、浴室、卧室、起居室,还有舒服的椅子、躺椅。如果住在高楼,可能会有电梯,「身体」可以很轻易的到达住处,这些设备都是为了身体,怪不得我们会视身体为自己,或认为身体属于我的?
我们对身体也有许多要求,希望身体不要太胖,太瘦;不要太高或太矮;不要有任何的疤痕或伤口,不要有缺陷(blemish)或骨折。即使是最轻微的苦,也不应该有,可惜身体总是不听话,而自认为拥有「身体」的人,对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关「拥有权」的问题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尤其在禅修结束时,当心比较平静和清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假设「我就是这个人」,而不会说:「我就是这个身体。」总会把自己想成是某人。我们需要客观的去观察身体的拥有者,要找身体很容易,看看它、摸摸它就行了,但谁拥有它呢?我们可以说拥有者是「我」。然而「我」又是甚么呢?在哪里?在哪里可以找到?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就知道不可能找到合理的答案,这是佛陀稍后会为布咤婆楼解释的。
告诉他人:「我是这个人」是一种谬误,是很难说服他人的。照镜子时,我们看到镜中的「我」,我们非常关心这个「我」,虽然我们的视力非常有限,只能看到外表,无法看到内心深处,可是我们仍深深相信「我」就是这个身体,并花许多时间来使身体更美好,这是认同身体就是我。要看出这种谬误,必须有平静的心和内观智慧。平静的心与内观智慧,会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
接着,佛陀向布咤婆楼解释「意所成我得」:
何者是意所成我得?意所成我得有形,肢节具足,诸根圆满者,意所成我得也。
在思考的过程中,常会有观察者和其他心理活动的存在。当我们认同(identify)观察者与我们的念头、反应、感受或其他的感官接触是「自我」时,这个自我就是「意所成我得」:把心、意当成自我。当我们修行一段时间后,我们会把「观察者、觉知者」视为自我。我们应该尽量深入观察,去找出这个觉知者,最后会发现并没有「人」存在,而我们假设它存在,所以佛陀才称之为我「得」(an “acquired” self)。
这种说法很先进,指出存在的真相,却不容易掌握,因为和一般人所相信的理论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观察这些信念所带来的苦。当我们发现苦就在心中,而不是「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苦就在我们内心,当我们知道苦及其原因,就能看到真相。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理念,以及所做的事是为了「自我」,那么必然有欲望。当我们了解这点,就略为了解佛陀的教导。
佛陀也认为这种说法很难令人接受。通常我们以180度相反的观点来看每件事物,很自然的,我们的问题来自相反的观点。所以当谈到究竟实相(absolute truth)时-即佛陀此处所说的法,我们不能以相对层次的问题来问。相对层次和绝对层次就像两条铁轨,永远平行,没有交集。例如,有人问:「如果没有自我,那么在静坐的是谁?」以相对层次而言,是「我」在打坐;以绝对层次而言,则「无我」。
当然,佛陀两个层次的法都教,当他教导正念、守护根门、正知或持戒时,是在相对层次说法,所以有个「我」在修行。我们必须仔细分辨这两个层次的法,当佛陀提到「我」时,不是「粗我」就是「意所成我」,我们不可以用日常的二元化的角度去理解。
我们必须接受佛陀所说的绝对层次的法,并以此来观察身心活动,以获得内观智慧;或是置之一旁,直到修行功夫深厚和禅定日深,可以修观为止。真正的选择只有这两个,第三个选择是加以否定,但这会有反效果,使我们在原地踏步,并深信有「自我」。后者是不理想的观点,因为我们经常要划分界线,将「自我」划在一边,而这世间是另一边。「自我」不只是旁观者、观察者,而且经常是有敌意的,因为外在世界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
由于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我们要面对二元世界时,有时会害怕,因为一个小人物要面对二元世界,会有无助感,该如何面对呢?有些人到了受不了时,会放弃面对;而大部分的人是转移目标,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这只是权宜之计,无法避免老、病、死,也无法对治我们的愚痴和不适当的反应,当然也无法去除苦。所以佛陀一再的说明「四圣谛」,除非我们了解第一圣谛:苦谛,否则根本无法入道。
我们对世间的反应只会带来更多的苦。我们相信在皮肤底下有一个自我,无论我们如何保护和珍惜,却往往无法如愿。在四个色界禅那也有「意所成我」只是此处的「意所成我」是纯粹的观察者,在四禅时,「意所成我」变得非常隐微,几乎不能觉察到。
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由意念所成的「自我」几乎无所不在,使人完全相信它的存在,因为我们一直感到它的存在,并一再的以它来活动,所以从不怀疑这个自我;直到我们遇上佛陀深湛的法。佛陀在此经中所说的法,大部份和相对层次有关,教我们如何把负面的念头改为正面的。此经在此处理佛法中最高深的部份。
此书所提到的,在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大部分没有详细的指导。从古至今,不同的神秘学家都试着表达此一层次的经验,但往往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所限制,所以难以窥知。另外,这类经验往往由顿悟而来,很难以文字形容,所以大部分的人不理会(ignore)这些经验,然而中古时代基督宗教神秘主义者、回教苏菲派(Sufi)和印度教大师的智慧语录,有关禅那经验的记载相当丰富。有些学者会加以研究,而对大部份的人而言,这个主题是毫无意义的,也没有兴趣,因此他们向外寻求,而非向内,希望能找到止息苦的方法。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想脱离苦,否则会苦恼不断,这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我们忘了我们的动机,我们有各种的观念和借口,如:「责任,事情总要有人做,可以增加知识,可以使自己快乐」等等。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解脱「苦」,那么,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有内观智慧。所以佛陀证悟的宣言都是与苦有关的,或许有人认为这是负面的,而佛陀只是把事实说出来,并说明超越苦的方法。
佛陀继续说:
何者是无形我得耶?无形之想所成者,无形我得也。
「无形我得」只能从无色界禅那中体验,因为「无形我得」既没有身体,也没有心识状态。在空无边处及识无边处没有任何边界,此时,只有想(perception)。如果没有「想」,我们将无法知道我们所体验到的「空无边处」及「识无边处」,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是「想」。
想、觉知和意识,是我们最后的凭借,如果放下「以身体为自我,以心为自我,以念头思想为自我,以感受为自我,以观察者为自我」的观念的话,只剩下意识,所以说「我」就是意识。
我们仍活在相对的、二元的层次中,只是不常发生。有「我的」想,这是与「你的」想相对的。或许「你」所进入的六禅有特殊的「想」,而「我」没有。所以「我的想」与你的不同,这也是二元的观念。这有两种不好的结果:一是优越感(我的境界比你高),二是自卑感(我不如你),两者都是不对的。
意识或想,没有其他的含意,这两个词我们都可以用,虽然「想」和「标明」有关,如我们在前文讨论「守护根门」时所说的,但此处所强调的是纯粹的觉知。
有个故事很贴切的说明不是二元的「想」。有位长老带几位年轻比丘到森林里散步,突然一群强盗把他们围住。强盗要求那位长老选一个人出来当人质,以便寺院交钱赎人。他们再一次问长老,但长老仍保持沉默。他们第三次问长老,长老仍然没有回答。这个时候,他们生气了,说道:「你怎么不答我们的问题?有什么问题?」长老回答说:「如果我指其中一位年轻比丘留下,那么他就是比较低下的;如果我让自己留下,那么我就变成比较低下的,而我和年轻比丘们事实上没有分别,所以不知道应该指哪个给你。」那群强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放了他们。
只要我们认为自我是存在的,无论是个体或个人的身份(identity)都是有限的,都非常依赖感官接触,因此,苦永远无法止息。佛陀接着说:
布咤婆楼,我之说法,实为欲使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悟,至于安乐。
接着佛陀用同样的话来说明如何断除「意所成我得」及「无形我得」。有些人把「断除粗我得」视为断灭,这是误解。在某些经典,佛陀说得更清楚:「我所说的法,是要断除粗我得的假象」。我们不是要断除生命或一些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要去除「自我」的假象。
在日常生活中,为甚么我们不能去除「自我」的假象?首先,我们必须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也就是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苦。其次,要知道如何对治这些苦。我们不能只说:「好吧,我不再相信有自我。」这是无法解脱苦的。我们必须体验到无我,至少一次,看看没有这个「自我的假象」是何等光景,我们必须禅修才可以做到。
这是佛陀教导禅那的原因,透过修习禅定和内观智慧,我们可以观察苦;我们可以体验片刻绝对的寂止,此时没有「想」,没有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只有解脱、自在、欢喜的感觉,以及对能证入实相的感恩心。要有这种境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我们必须入定,心必须专注一境,不动摇,不散乱;其次,我们对自己能觉悟要有信心,一旦体验到安止定,我们会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佛陀所说的法,我们可以用来去除「自我」的假象,以便「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悟,住于安乐。」除了智慧以外,我们也可以用观智(insight)一词,两者互通,或说是「内观智慧」。透过高超的智(super-knowkedge)所证得的智慧很重要,这种智无法从仪式、上师或信仰获得,只能从修行中获得。「高超的智」非普通的智,它与我们的经验有关,对「自我」的意义没有任何疑惑,做个过来人有「了解的体验」。佛陀自称为「指路人」,所有的导师只能指路,走不走就靠我们自己。
在佛陀时代,有许多人第一次听佛陀说法就开悟了,这是佛陀特有的智慧,能启发信众。在东方,人们比较有宗教热诚,西方人这方面就比较难做到。虽然我们无法听陀佛说法,但可以阅读佛陀留下来的许多开示和修行上的指导,我们只要跟随他的道迹就行了。
我们透过高超的智「证悟和获得」智慧。「证悟」指有所体验;「获得」指我们对它有深入的了解。接着,佛陀说:「断离染污法」,一旦「自我」的假象消失,我们的心就不会再有负面情绪,我们一再的观察心,就可以得知这善果有多大,这叫做「审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
佛陀说:代替「断离染污法」的是「增长清净法」,所有的贪与嗔都来自「自我」的假象,一旦自我的假象消失,内心剩下的只有纯洁和明净。
「自我」需要保护,需要感官的满足,也需要安全,然而这个世间哪里有真正的安全?我们买不到,却让保险公司赚了一大笔,而内心深处仍缺乏安全感,是谁在感受?当然是「自我」了。然而,如果没有「自我」,就没有「人」需要安全感了。
身和心只是身心而已,自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对这种说法强烈抗拒的话,这表示我们对自我的执着是多么强。我们要做的是多体会苦,当我们感受到苦时,会问:「为甚么会有这些苦?一定是某人或某事使我受苦。」直到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其实,苦在心中。
遵循佛陀的教导,也就是依法修行。当我们修行日久,事情会改变,「清净法」会增长。内心会净化,不论是理智的心(mind)或情感的心(heart),由「以善心代替恶心」开始,也就是以正面的心态来代替负面的心理反应,例如,「厌恶、嗔恨、抗拒、反抗」,无论我们认为这些负面情绪的生起是多么的有理由,这些负面情绪也会带来许多不快,所以只有愚昧的人才会执着它们。一旦我们学会「以善心代替恶心」,而且能运用自如,我们便可以去除负面的情绪,让快乐的心境生起。
在这个世间,在任何城市,当我们走在街上并观察人们的脸,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张快乐的脸,快乐远离人们,因为人们的心中充满贪欲。佛陀说:只要能放下「自我」,会使「染污法消失」,那么「清净法就会增长」。我们发现所有不愉快的心境都和「自我」有关。通常我们认为所有负面的情绪都由外境引发,例如,有人做了令人不愉快的事,即使不是针对自己,我们也会生气和不快,这就是「染污法」。这种情绪反应会带来伤害,而且毫无用处。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去为「自我」找借口;如果有,那只是「自我」在作祟罢了。佛陀继续说:
布咤婆楼,汝意或谓:「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欲自证悟,至于安住,然而(有情)犹住苦中。」布咤婆楼,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能自证悟,而自安住,是则愉悦欢喜,成就轻安,又得正念正知,住于安乐。
布咤婆楼还没有开始修行,所以不知道「断除染污法」是什么滋味,佛陀把布咤婆楼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先说了,佛陀告诉他:如果认为此时会不快乐是错的。佛陀说:快乐不是指喜悦兴奋的心境。当我们有了正知正念和平静所生起的舍心(equanimity),这种舍心会带来平静之乐。
千万不要混淆「舍心」和「冷漠」,一般人很容易混淆。冷漠指我们不去面对所发生的事,「舍心」指以正念正知和平静的心来面对所发生的事。
对禅修的目标(所缘境)保持觉知,可以培养正念,在日常生活中应尽可能保持正念,无论做什么都要保持正念。当心没有任何杂染,正念正知就会现前。其实正知(clear awareness)是内观智慧的别称。「正知」不只向内观察自己,同时也使我们以悲心而不是以责怪及厌恶的心,来观察他人及其行为。
当心清明时,只会认知、观察,不会抗拒。这里提到的平静是舍心的一部份。我们在禅修时修习舍心,并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渐渐的舍心就成为我们的心境。
接着,佛陀继续说明去除「粗我得」的方法;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去除「意所成我得」和「无形我得」。佛陀说:
布咤婆楼,若有人向我问曰:「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耶?」于如是问,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欲使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此处的「粗我得」指「这个人是」,指我们自己。佛陀又提到「意所成我得」及「无形我得」。换句话说,这三种「自我」都是假象,无论在身、心或意识中都没有「我」,在我们身上也找不到一个「拥有者」,所以不能说「我是拥有者」;在这三种自我中,也找不到观察者,所以不能说「我是觉知者」,因为这只是心的作用-行蕴(mental formation)罢了。接着,佛陀问布咤婆楼:
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我之所说,合正理否?
世尊所说,实合正理也。
佛陀解释说:
布咤婆楼,犹如树立一梯于殿堂下,欲登一殿堂,旁人问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东方耶?在西方耶?在南方耶?抑北方耶?高耶低耶?抑适中耶?君知之乎?」彼答问言:「我欲立梯于殿堂下,为欲如是而登殿堂。」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否?
世尊,彼之所说,实合正理也。
布咤婆楼,此亦如是,设若有人,向我问言:「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粗我得?云何永断意所成我得?云何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悟,至安住耶?」于如是问,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永断是粗我得,…永断意所成我得,…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除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悟,如是乃至住于安乐。」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我之所说,合正理否?
世尊所说,实合正理也。
佛陀尚未叫布咤婆楼去修习,只是让他去思考是否合理,而布咤婆楼表示这种说法合理。
当我们能放下这些假设的自我,「染污法」就会消失,而能于当下「清净和智慧充广」,这点很重要,我们不只能获得智慧,还能安住其中。内观智慧是不会退失的,而平静和轻安的禅那境界很容易退失-如果我们不禅修的话。当我们获得内观智慧,整个人的态度、威仪和内心的感受都会改变。如果我们真的沉入内观,内观智慧便永远不会退失。所以在修习安止定后,我们会自问:「我刚刚学到了甚么?从禅修中获得哪种内观智慧?」佛陀所教导布咤婆楼的法,还未能改变他,布咤婆楼必须先对法生起信心,才会开始修习。而改变前需要先对修行有所体验,即是所谓的「了解的体验」(understood experience)。在心已经平静到某种程度时,我们应该自我审察:「我的苦如何形成?苦生起时,我能觉察到吗?」或是「我所关心的自我到底在哪里?找得到吗?」或是「我是否了解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我对事物的了解有没有因而改变?」在三法印中,除了观察无常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其他二种:苦与无我。心平静时,能够保持客观,并且能够放下我们所接触的二元的、相对的事物。有了平静的心,我们会放下一些执着,并能更清楚的观察世事。
以上所说的各种阶段,引领我们走上清净之道,并证得内观智慧。当然,「于现法中,智慧充广」是开悟的最后阶段,而心清净是先决条件。如果心不够清净,就无法客观的观察。禅修使心清净,所以我们必须禅修。透过一再的修习,不断的观察,每个阶段的内观智慧会慢慢增长,而我们也可以随时应用内观智慧。
第十二章
何者是真正的自我?
象首加入了对话,并提出有关「自我」的新的问题。当想到「我们是谁」,这种难以理解的问题,象首、布咤婆楼和我们其实都差不多,经常会有新的想法。
时,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
「世尊,粗我得存在时,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无形我得之存在亦虚。此时,唯粗我得之存在为实耶?
世尊,意所成我得存在时,粗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无形我得之存在亦虚。此时,唯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为实耶?
世尊,无形我得存在时,粗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亦虚。此时,唯无形我得之存在为实耶?」象首问:如果只有一种「自我」,其他两种又如何?象首认为三种「自我」都存在。我们可能会认同他的看法。例如,当我们走路时,不小心被树根绊倒,脚受伤,流血了,我们会自言自语:「我的脚受伤了,要马上处理。」于是去药房买药膏涂,但一会儿又痛起来,我们会想:「真的痛得很厉害,看来只涂药膏是不够的。」于是去按摩或针灸,或做其他的治疗。这时候我们所认同的自我是「粗我得」,以身体为自我。此经的翻译比较学术化,用「粗我得」是为了符合巴利文的原意,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们有时也用其他的翻译。
我们经常以自己的身体为「自我」,例如,吃饭时,我们会想:「我肚子饿,想吃些东西。」饭后,我们会说:「好像不太饱,我想多吃点。」我们关心的是「我的」肚子饿,「我的」身体,「我的」胃。
象首问佛陀:这三种自我是否同时存在,佛陀回答:
象首,粗我得存在时,唯名为粗我得,决不名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在时,唯名为意所成我得,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
象首,无形我得存在时,唯名为无形我得,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意所成我得。
很明显的,我们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自我。尤其是当身体感到疼痛或愉快时,我们就会视身体为自我。身体很少有不苦不乐的时候,一旦有较强烈的感受,我们马上会把身体视为自我。禅修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们马上就会关心起来,除非定力非常强,不受影响。我们很容易视身体为自我,一次感冒,一阵咳嗽,「粗我得」立刻生起-是「我」在感冒、咳嗽。
另外,我们也把「意所成我得」(mind-made self)视为自我,例如,我们精进的持戒,就会想:「真好,我一直在持戒。」持戒是好事,但说这话时,我们认同的是甚么?肯定是「我」,是「我」在持戒,是「我」在想这件事。有时在禅修时,我们的心充满妄念,无法入定,因此很烦恼。妄念一再生起,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些妄念,也认为这些妄念是我的。在相对的层次中,我们认为是「我」想禅修,是「我」被这些妄念所干扰,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可能吗?
这种「意所成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也是观察者和记忆者。例如,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我」,有此念头时,此刻的「意所成我」想起了另一个「意所成我」,所以有两个意所成我。当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会说:「有人正在回忆,那个人就是我。」我们忘了记忆只是记忆而己,别无他物。或者我们会向前瞻望,为将来的「我」打算,此时,有两个「我」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我们只知道是「我」在计划未来。我们知道「为将来打算」会干扰禅修,却又认为这是愉快的休闲,让我们暂时忘记身体的疼痛。基本上,「意所成我」是心的作用,是心在说:「这是我。」事实上「意所成我」总是存在着,「意所成我」从一醒来就出现。当我们醒来时,第一个念头是甚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正念,或许能觉察到,脑袋本来空空的,突然心理活动开始了:「现在几点了?我今天要做甚么?我会迟到吗?会感冒吗?」这些都是心在活动,身体只负责张开眼睛,所有这些心理活动都在支持「我」的存在。这个「我」也在找寻脱苦的舱口,于是所有的掉举、不安、担忧、计划、回忆,随之生起,可惜这些心理现象无法解脱苦,或许能暂时避开苦,所以是一条死胡同。潜藏的苦永远存在,只要为琐事操心、不安,苦就会生起;每当我们计划未来时,就必需面对这些苦,所以我们会想:「今天,我要做甚么?我要上班,之后,要好好散步,或约朋友一起用餐。」我们最关心的是「意所成我」,意所成我是三种「自我」中最难去除的,我们可能认为:「我知道这些道理。」而谁是那个知道者(knower)?拉玛那.马哈希(Ramana Maharshi)是南印度已开悟的圣者,于五十年代去世,他的教法非常简单,只问:「我是谁?」这相当难掌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或透过其他的训练,甚至要花好几世的时间。他的弟子尼萨迦达他(Sri Nisargadatta Maharaj)只教导「我是这。」(I am that.)以及放下所有事物。
修行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重点,佛陀以听众可以接受的方法指出这一点:如果想追求真正的快乐,唯一的方法是放下那个不快乐的人,而不是执着那个快乐的人。当那个不快乐的人消失了,就会有由平静及纯然的觉知所生起的快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许多机会来观察这「意所成我」,例如:「明年我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怎样处理才合我心意?」心不停的搅动,追寻,无法平静下来。
了解这些,并非指我们能去除「意所成我」,但已经向前迈一大步。如果我们无法觉知「意所成我」,就会随着本能或冲动行事,永远是凡夫,只会跟随大众行动。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不满,但仍会逃避苦,因此心无法安住在当下,一旦心想逃避现实就会产生苦。当我们发现这是「意所成我」的作用,心就会安住在当下,所以要先知道心的状态,然后再采取行动。
当我们能觉知「意所成我」时,就会生起另一个层次的认知(recognition)。这并不是说:我们能立刻去除「意所成我」,但已经接处到边缘了。在去除「意所成我」之前,去观察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在想,我在观察,我很专注,我的心不够专注。」这些都和「我」有关,可以归纳为三种:「我现在…」或「我将…」或「我已经…」。
佛陀说:
象首,设若有人,向汝问言:「汝曾存于过去世,汝非已有否?汝将存于未来世,汝非当有否?汝存于现在,汝非今有否?」象首,有如是问者,汝云何答?
世尊,有如是问者,我当答言:「我曾存于过去世,非不存在;我将存于未来世,非不存在;我现在存在,非不存在。」世尊,于如是问者,我当如是答。
象首和我们一样,认为他的「自我」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存在。这些都不是新的论调,佛陀会教他完全不同的法。
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我」,人们有许多设想(assumption)。首先,我们在划分界限。「过去的我」存在回忆中;「现在的我」很少被观察到,我们隐约感到它的存在,却难以窥知;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未来的我」,未来的我会做许多美好的事,会比较快乐,能够入定等等。我们把这三个「自我」都称为「我」,而实际的情况则更复杂。当我们把过去带到现在时(即回忆过去),过去的我就变成现在的我。同样的,当我们把未来的我带回当下,那么未来的我就变成现在的我,所以我们不但把自我划分成三个,也把时间划分成三部份。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完美,因为活着就有体验(苦乐参半),而我们唯一能体验的是当下这一刻,其他的不是记忆就是希望。
把自我和时间分成三个部份后,我们发现:我们焦虑的期待未来,或充满懊悔的回想过去,因此快乐离我们而去。每当我们把自我分成三个部份,便没有空间让快乐生起,虽然有可能生起乐趣(pleasure),但这不是快乐。快乐与内心的喜悦、平静有关。把自我分成三个部份并不能产生平静。然而,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过生活,所以我们无法觉知这是徒劳无功的,是多么的虚幻。我们一直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直到接触佛法,我们才知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透过正念和禅修,我们可以觉知当下的身心状态,尽管只是片刻,我们都能体会活在当下的滋味。过去的已过去,未来的尚未到来,只有当下可以掌握。
象首和我们一样,仍然执着由时间所划分的「自我」,佛陀试着以比较逻辑的方法,让他看到真相:
象首,又若问汝:「汝存于『过去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未来(我得)为虚,现在(我得)亦虚耶?
复次,汝将存于『未来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我得)为虚,现在(我得)亦虚耶?
复次,汝存于『现在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我得)为虚,未来(我得)亦虚耶?」象首,有是问者,汝云何答?
世尊,若问我言:「汝存于『过去我得』时,如是乃至汝存于『现在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未来者亦虚耶?」世尊,有是问者,我当答言:「我存于『过去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未来者为虚,现在者亦虚也。
复次,我将存于『未来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现在者亦虚也。
复次,我存于『现在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未来者亦虚也。」于如是问者,我当作是答。
听了佛陀的解释后,象首知道不可能有三个「自我」同时存在。现在,他认为只有一个「自我」存在,分别是过去的自我,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之前,他以为有三个自我,现在只剩一个;而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有三个「自我」。
如果我们看以前的相片时,我们看到甚么?除了朋友外,就只有过去的「我」。这也是我们拍照的原因:过去不会随着时间消失。我们会说:「这是我。」我们和象首开始时一样,将「自我」分成三个部份;如果加上身体和心就有五个「自我」;如果再加上时间的话,「自我」随着时间又分成:久远的过去,不久的过去,昨天等,那么就会有数百个过去的「我」,就像相片簿中的照片一样。最后「我」多得连自己也数不清,究竟哪个「我」是自己。如果佛陀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也会和象首一样回答,我们知道不可能有数百个「我」同时存在,甚至连三、四个「我」都不可能,最后我们会说:「只有一个我,就是当下在觉知的那个。」象首知道不可能有三个「自我」同时存在,只有当下的「自我」存在。想想看有许多「自我」消失在过去,而有许多「自我」在未来出现,我们想想就知道这是很荒谬的,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说法,所以只能接受这种说法。
过去有些神秘学家有不同的体验,也知道这种自我观的谬误之处,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它的原因只有一个:「有爱」。如果我们能去除「有爱」,就不会有类似的烦恼。看破有爱的方法是去观察「自我」如何使「有爱」生起;也可以看看「有爱」如何使「自我」生起。两者是同生同灭,所以不能说哪个先,哪个后。
象首知道他就是当下的这个「自我」,我们或许同意这种看法。他现在仍有「无形我得」要处理,「无形我得」是我们的意识。既然我们不是身体,也不是心,那么我们一定是意识了。有一种意识是在禅那中的意识,因此这种禅那也称为世间禅那,而非出世间禅那,因为仍有「自我」。
所有的禅那都有同样的性质:有时强,有时弱。前三个禅那的「自我」非常明显,第四禅就比较不明显,第五至第七禅比较强,只是层次不同,是比较高超的意识,但「自我」仍存在,仍在觉知这些禅那。在第八禅,自我意识变得非常弱。我们知道:在禅那时,身体意识是不存在的。另外也没有「意所成我」,如果有任何念头,禅那就会终止。在禅那中有一种高超的意识,我们喜欢认同这种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最令人满足的,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有些人做不到。很明显的,这种意识是某人的,也就是「我」的。
退出禅那后,有另一种意识存在,也就是「我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我们通常称之为观察者,这种意识是我们强烈认同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放弃以身体为「自我」,或放弃以心的四个层面(即受、想、行、识)为「自我」,我们会发现仍有某种东西叫做「自我」。
我们的「有爱」会说:「如果没有我,我(有爱)就会消失。」所以我们选择更微细的「我」-意识,这就是「无形我得」。在理智上,我们或许会放下其他两种「我得」,事实上可能甚么也没放下。如果像象首一样被问及,我们可能会和他一样诉诸「观察者意识」。我们认为,这种观察者意识和其他的心的状态不同。有感官意识,有感受、想、行,而观察者被区分出来,以便观察其他的心理状态,我们却忘了「观察者意识」也是心识作用的一部份。
象首接受只有一个「自我」存在,并能于当下体会。他同意有三个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佛陀接着为他解释:
象首,譬如由牛有乳,乳变为酪,酪为生酥,生酥为熟酥,熟酥为醍醐。当有乳时,唯名为乳,决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不名醍醐。当有酪时,乃至有生酥时,乃至有醍醐时,唯名醍醐,决不名乳,亦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
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时,决不名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唯名为粗我得也。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时,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唯名为意所成我得也。
象首,无形我得存时,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意所成我得,唯名为无形我得也。…象首,凡此等等为世间共相,世间言语,世间名称,世间记述法,如来用之,正当者也。
在这里,佛陀有很重要的开示。佛陀告诉象首:这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相信的,而就绝对层次而言,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佛陀能看到实相,并以世俗的语言表达,不会误用。由于布咤婆楼和象首一时无法掌握绝对层次的法,所以佛陀只用相对层次的语言来说明,佛经中经常提到佛陀会按照听众的能力来说法:
我佛无上师,所说二谛者。
真谛与俗谛,而无第三谛。
俗谛世间用,于世而为真。
真谛无上谛,于法而为真。
佛为世间解,用而无妄言。
世俗层次的语言并非妄语,而是我们如何看事情和互相了解的方式。然而有其他的方式,也就是绝对的层次,诸法实相的层次。当Dhammas中的d和s是小写时,指现象;当D是大写,而没有s时,指佛陀的教法(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真理或自然的法则。
如果象首能了解只有一个短暂的「自我」存在,佛陀就已经很满意了。佛陀为象首举了将牛奶酿成酥的比喻,希望他能了解在同一时刻,我们只有一个「自我」。佛陀的说法到此为止,佛陀并未说明:在绝对的层次,连这个短暂的「自我」也是假象。佛陀知道,首先要让象首和布咤婆楼迈向修行的道路,否则,他们只会停留在知性的层面,继续找新的话题来辩论,最后将一无所获。因为去问「什么是自我?」,「为什么没有自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所喜欢的自我,而不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些问题无法生起内观智慧。希望有个自己喜欢的「自我」,这种想法与灵魂的观念有关,也是另一种「我见」。我们视灵魂为良善的「自我」,而不喜欢的部份就不是「自我」。所有人都曾堕入类似的陷阱,在这问题上,世人都是一样的。
现在经文即将结束,传统上经文末段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为佛陀入般涅盘后的二百五十年间,经文都是靠口口相传的,之后才以文字记载,所以经文结尾都大同小异,以免有任何错误。
世尊如是说已,布咤婆楼苦行外道曰:「伟哉世尊!大哉世尊!犹如使倒者得起,闭者得开,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灯,有目得视。世尊以无数方便,说示教法,亦复如是。世尊,我今归依佛陀,归依法,归依僧众。唯愿世尊,听摄受我,自今已后,尽寿归依,为优婆塞。」在此处,布咤婆楼已经完全信服佛陀所说,并希望成为在家弟子,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表示投入修行,护持和信受佛法,表示已经找到情感和心灵的庇护所,能带来极大的喜乐。今天我们也同样皈依三宝,只是布咤婆楼能见到佛陀本人和皈依佛陀。佛陀是位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是人,经过修行后,证得正等正觉。皈依佛,就是以热诚、敬爱和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些事实。我们也皈依法,皈依法是以「法」作为生活的指导和获得幸福的最高原则。我们也皈依僧伽,皈依那些已经开悟的僧众,以及已经弘扬佛法逾二千五百年的僧众,他们使佛法能留传至今。
当我们皈依三宝时,充满感恩、热诚和投入。如果我们能依法修行,并了解佛法的话,我们可以避免来自世间和自己本能(instincts)的危险。皈依可以使我们坚定不移,使我们继续修行。大部的人很难坚持修行,因为必须从世俗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所以常常是断断续续的。
有些东西比我们伟大多了,记住这点对修行很有帮助,因为谦虚感会在心中生起,这和自卑完全相反,自卑意味着「我比你差」;而谦虚是指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谦虚是朝向「无我」的重要一步。有些人自认为很重要,而一个谦虚的人就不会如此。只要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就不可能放下「自我」。谦虚是修行的一部份,使我们能如实的了解自己。谦虚的人不会自责,不会感到自己没有价值。真正谦虚的人会知道自己是凡人,会有凡人的愚蠢。即使在表面上,我们不再做一些愚昧的行为,由于我们的心仍然不够清明和完美,所以难免有一些愚蠢的念头。当我们认识到佛陀的究竟清净和谦虚,就会受到启发,并向他学习。
布咤婆楼就是这样,他发愿「尽形寿」皈依三宝。当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时,切莫半心半意的,或只是一时兴起就去皈依。我们皈依是为了在生活中实践。
此时,象首也有话要说,一开始和布咤婆楼说的一样:
伟哉世尊!大哉世尊!犹如使倒者得起,闭者得开,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灯,有目得视。世尊以无数方便,说示教法,亦复如是。世尊,我今归依佛陀,归依法,归依僧众。
接着,象首又说:
唯愿世尊,许我等于世尊所,得出家受具戒。
象首请求成为比丘〈bhikkhu〉。那时候出家是件容易的事,佛陀只要说「善来比丘」就行了;现在出家有许多仪式,还有许多戒律。早期的僧伽并没有戒律,因为没有比丘有不当的行为,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僧团,情况改变了,每当有人犯错,佛陀就会制定新的戒条,日积月累,由75条至115条、150条,最后有227条。假如佛陀活在今日社会,可能会制定更多戒律。
有些戒律已不适合现代社会,毕竟二千多年前的印度社会和现在的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当然,一些重要的戒仍然有效,而一些小戒已经不合时宜。佛陀制戒非常仔细,函盖了生活上的每个细节,例如有些戒律规定比丘如厕时,要小心,不要伤害小动物。当佛陀无法亲自处理每件事时,就制定出家仪式让人遵守,让一些够资格的长老代替佛陀主持出家仪式,这些仪式和现在的差不多。
于是,象首舍利弗,于世尊所,出家受具戒。
出家,指由在家生活转变为无家的生活,不是要住在没有屋顶遮头的地方,而是不再有家庭生活,不再有私人财物。有段时间僧伽的确没有任何地方可住,后来才有寺院,出家人才有茅蓬(kutis)可住。
受具戒后,尊者象首舍利弗,即独处,心不放逸,殷勤专念,精勤止住。为良家子出家所求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彼为时未久,即于此时,自身证得超越之智,安住其中,自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生已尽,梵行已立」,修行到了极致时,不会感到在身心中有个人,有个体存在。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体验,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然而我们可以推知:不再有「我」,所以没有「我」在担忧,在计划、在回忆和需要安全感,只有身和心去做一些该做的事而已。佛陀说法四十五年,也是处于这种状态。「生已尽」是因为「生」是由「有爱」所引起的,而有爱是由「我」引起的。如果没有「自我」,就没有贪爱,也不会再生(rebirth)了。正如婆蹉衢多的故事一样,没有木柴,火焰自然会熄灭。最后,经文提到:
尊者象首舍利弗,成阿罗汉。
象首是大象训练师,在当时的印度是收入丰厚的职业,斯里兰卡语是mahout,即使现在仍是非常重要的职业。经中经常提到「良家子」,这并非指那个人来自富有或较高种姓的家庭。佛陀不重视种姓,任何种姓的人都可以成为佛陀的弟子,都可以出家,例如扫街的人或理发师,这两种人在古印度是阶级很低的,而佛陀也会让他们加入僧团。佛陀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而不是他的种姓。所以「良家子」指此人来自一个善于照顾小孩的家庭。
经文告诉我们,出家的目的是要成为阿罗汉,象首知道「即于此时,自身证得超越之智,成为阿罗汉-这是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在经中,不再提及主角布咤婆楼,我们只知道他皈依了,希望他也在修行。而在经文结束前出现的象首是完全献身于修行。
以上经文的结尾是大部分经文结束的方式,也就是以「有人请求出家」来结束经文。
纵观全经,我们知道要改变一个观念错误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佛陀亲自出马也不例外。「自我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已根深蒂固,让我们很容易执着身体、心或意识为「自我」;或执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我」。那些喜欢思辩的人会去分析和思考此经,然而,他们将一无所获。当然也有人甚么也不做,因为他们看不出修行有甚么利益,所以他们会放下这部经。
虽然本经的小标题是「心识的各种层次」,而事实上是在讨论「自我」的意识。
第十三章
道及果:修行的终点
《布咤婆楼经》从修行的起点说到修行的终点,详细指导应如何禅修,分别是持戒、修定及修习内观智慧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遵循这些指导的成果。最后生起的内观智慧能观察「自我」的虚幻不实,进而彻底放下自我。
在这部经中,我们知道不可能有许多「自我」,每一刻只有一个「我」,生起又消失,新的我又出现。首先出现的是以身体为「自我」,把身体视为「我」;然后,意所成我(mind-made self)会出现,这是把心理活动视为「自我」,当我们的意识执取某种事物时,这种意所成我也会消失。这些「自我」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都是不坚固的,都会消失。片刻之前我们有个「自我」,现在我们有另一个「自我」。我们可以回想之前的那些「自我」,并问自己:那些过去的「自我」现在在哪里?就如想起自己曾做过某件事,而那件事现在是不会再做的。那么究竟哪个「自我」才是真的?是过去的我或现在的我?我们永远无法抓住「自我」,因为自我经常在变动。自我就像一条小溪,如果我们想抓住溪水,我们把手放到水里,试着去抓溪水,将一无所获。溪水不断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那么就不是流水,而是一潭死水。
当我们知道「自我」是假象,并了解其性质时,就需要不同的方法来修行。有些人透过觉知「苦」来观察自我,厌恶自己的苦,所以每当「自我」体验到苦时,就能放下「自我」。有些人则看到自我中无常的特质,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有些人则会分析「自我」为何物,他们发现自我是不真实,不坚固,不可靠的。有些人则同时用这三种观法,也就是观察自我的特质-无常、苦和无我(没有实体),这是内观智慧禅的精髓(essence)。
在修行时,把无常、苦、无我这三法印铭记在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世俗的生活中,许多事物看起来好像是恒常的,能够带来满足;好像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可界定的个体。所以世俗的生活对修行没有帮助。我们必须记住这三法印,并用来观察我们的身心,观察我们的感官经验和所有的念头。如果忘了去观察,就等于忘了修行。
修行不只是禅修而已,虽然禅修是修行的重心,如果不禅修的话,心会坚如盘石,很难改变。除了禅修外,我们也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和随之而来的行动。看看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看到苦的实相而想离苦?还是想寻求短暂的快乐来逃避苦?我们选择哪一种?如果想要知道实相,我们必须去寻找。我们的心好像围了一层面纱,一层雾或一道砖墙般,难以窥见。我们或许是禅修者,但仍然是凡夫(puthujjana),也就是尚未证得「道」与「果」的凡夫。「道」与「果」是精进修行的结果。
道心(path moment)巴利文是magga,道心生起后会生起果心(fruit moment),巴利语是phala,合称为道果(magga- phala),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当道心与果心生起时,禅修者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成为圣者(Ariya),是真正的佛陀的弟子。
我们怎样才能证得「道心」?除非我们修习禅那和内观智慧禅,并勘破「自我」的虚幻不实,这指我们必须从基础修学起,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种事实,对于解脱之道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否则不能证得道智。我们相信所谓「自我」只是一种概念而已,其他人相信与否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以自问:「那些相信有『自我』的人快乐满足吗?抑或他们的『自我』的观念正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当我们深信无我,就会放下虚妄不实的自我,证得道心时,便能做到;放下自我并不容易,但至少我们知道要如何放下。
获得道心的最佳时刻是禅那后,佛陀说在任何禅那后都可以证得道心,而三禅、四禅、五禅、六禅及七禅最适合,因为此时的心特别平静,没有五盖。当五盖生起时,我们无法看清实相,刚退出禅那,没有五盖,心特别平静清明,能够体验到不同层次的境界。事实上,在修习安止定后,除非入定的时间很长,心非常平静、稳定,否则五盖仍会生起,这时是不可能证得「道智」的。所以内心不受干扰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知道心中没有五盖时,我们可以再度观察自我的三种特性(无常、苦、没有实体),直到了解「自我」只是假象罢了,除了假象外,别无其他,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这由感受及意识组成的「自我」。当心毫无疑惑,能了解自我是一切苦的根源,而自我会不断改变,并没有不变的实体;同时也知道:放下自我是修行的目的。
接着我们可以作意,把心导向寂止(still-point),此时心没有任何活动,处于寂止状态。心必须没有五盖,没有任何疑惑,例如,「或许是『我』想去除某些东西」,若有这种念头,心就无法平静。如果心是平静的,自然会寂止,此时没有任何心理活动,所以也没有体验者(experiencer),我们无法叙述道心,只能说此时所有的心理活动完全寂止。这和第七禅「无所有处定」的体验有所不同,因为在禅那中,仍有一个体验者,体验到一切法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而当道心生起时,一切寂止,连体验者也不存在。
紧随「道心」而起的是「果心」,由于「果心」有某些特性,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经验的老师可以以此来判断弟子的修证境界,看看弟子是己经证得,差不多证得,或只是想象出来的境界。并非所有的特质都会出现在每个人每次的经验上,但有些特质总会生起。证得果心时,会大喜,充满喜悦,会有完全的解脱感,就像我们放下巨大的负担一样。这种解脱感非常强烈,可能会使我们流泪,这不是伤心的泪水,而是从巨大的压力、苦迫中解脱出来的感觉。这种喜乐的感受可能稍后才会生起,虽然果心随着道心立刻生起,而大喜则未必立刻生起,可能在第二天,当心再度体验解脱时才会生起。
当道心与果心生起时,智也会生起。例如,在某一时刻,没有人存在,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深湛的智。在第一次证得果心时,这种体验特别明显,因为那时「自我」完全消失。
我们知道一个心识剎那(a mind-moment)是多么短暂。「觉知」与「解脱」占去两个剎那,最多不超过三个剎那。那种解脱感、自在感以及伴随的泪水,如果没有立刻生起,稍后可能会变成大喜。而「觉知」会立刻生起,我们会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事,并了解修行所为何事,有时会感到身体失去重量,身体好像轻了许多,这是因为心「轻」了,影响到身体。
西元五世纪,觉音尊者在斯里兰卡编纂的《清净道论》是一本非常厚的书,此书总结佛陀有关修行的教导。这本书不容易读,因为非常详细,却是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而且有许多譬喻,其中有个过河的譬喻形容得非常贴切:
觉音论师提到一条河,河的两岸分别代表世俗生活与涅盘。靠近河岸有一颗巨大的树,树枝上有条绳索吊着,人拉着绳索就可以从世俗的河岸吊到涅盘的彼岸去。树枝代表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以身体为自我。在修行过程中,当我们想起「我」在修行时,这是以色身为我;而那条绑在树上的绳索代表自我的观念。我们抓着绳索,用力把身体摇到对岸,这代表修行。当冲力足够时,在适当的时刻,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我,就会降落到对岸去。
这只是一则譬喻,却非常有用。当我们落在对岸,刚开始会立足不稳,因为这是以往从未遇过的新处境,所以必须稳定下来。在体验过道心后,我们会感到心神不宁,好像发生重大的事情,却难以形容,因为既不乐,也非不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人就很稳定,而有些人要一两天才回过神来,有些人则需要老师的帮忙。然后,我们就可以快乐的欣赏彼岸的风光。我们已经变成不同的人,表面上我们和以前完全一样,除了我们的老师外,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内心的变化,只有自己知道。
初次证得道智及果智(初果)时,自然会破除十结中的前三结。佛陀说:这十结使我们不断的生死轮回,这十结包括:一、身见(我见);二、戒禁取见;三、疑;四、贪;五、嗔;六、色贪(有爱);七、无色贪(无有爱);八、慢(conceit);九、掉举;十、无明。这十结把我们束缚在有为法中。佛陀把他儿子命名为罗睺罗,意为「结」(fetter)。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这些结,使我们能究竟解脱。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是身见。去除身见以后,我们不再相信有个「自我」透过我们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透过我们的心去想,透过我们的欲望去渴求。我们不相信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自我」是错误的认知,是一种假象。只有证得初果,有第一种果心的人才有此正见。虽然内心的感受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但仍未将内心深处的自我感去除,但稍后会做到。当初果圣者自问「我是谁」时,会知道身心的活动并没有「自我」,也知道「自我」是由贪爱所生,而贪爱就是苦,而自我的观念是一切苦的根源,世人也因此受苦。
证得初果的圣者,身见或我见永远不会再生起,当我们在行走时,或与人交谈时,仍然有个「人」在那里的感觉。证得初果后,我们必须把有关自我的正见尽可能铭记在心,尤其是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时,因此时的我执比较强烈,如果忘失了这最深湛的内观智慧,那么就会有负面反应,因为证得初果,贪与嗔仍未断除。提起正见(right view)是修行不可或缺的要素。
证得初果的圣者称为须陀洹或预流者,指已经预入圣者之流,不会退转的人。经中提到须陀洹最多再轮回七次便可究竟解脱,甚至可以在此生证得涅盘。证得初果的人,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敏感,知道心中仍有贪与嗔,并下定决心继续修行,以断除其他的烦恼,因此修行又有了动力。
预流者也已去除另外两个结,其中一个是疑。疑是修行的障碍,使我们不去做该做的事,思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做,我们浪费许多心力和时间,甚至放弃修行。当我们首次经历道心及果心,对佛法就不会有任何疑惑。所有对佛、法、僧的疑惑会完全消失。佛陀所说的「无我」,现在我们已经亲自体验到了,这种经验是非常美好的,且远远超过任何安止定的经验。我们信心十足,感恩,并有强烈的决心。
经中提到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在一次的禅定中证得四种道心和果心,包括初果(须沱洹),二果(斯陀含,一来者),三果(阿那含,不还者)及四果(阿罗汉)。对我们而言,能证得初果是伟大的成就,而证得初果的圣人很少会就此停住,因为心可以继续向前。另外一种疑惑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这种疑惑也已去除,由于我们有超越一般意识的经验,所以会充满自信。
自信不是一种优越感,优越感通常随着自卑感生起。此时所产生的自信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毋需向任何人证明,因为既然无我,也就没有事情需要证明,也无处可去,因为没有「人」存在。这种内在的肯定能帮助我们去修行,并对佛、法、僧三宝生起信心和热诚。
预流者所断除的第三个结是戒禁取见(the belief in rites and rituals)。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相信借着某些仪式可以净化我们自己,甚至使我们解脱苦。虽然佛陀否认宗教仪式有这种力量,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和现代社会,这种戒禁取见仍广为流行。证得初果后,我们会完全舍弃这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证得初果是修行的结果,和宗教仪式毫无关系,而与我们的心是否清净,是否愿意放下自我有关。
去除「戒禁取见」并非指我们不再做任何仪式,而是我们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宗教仪式上,所以会把宗教仪式减到最少。如果以正念去从事宗教仪式,有些仪式的确有净化心灵的作用,例如诵经或礼敬佛、法、僧,但我们必须要有正念,而不是以刻板的形式来进行这些仪式。诵咒(mantras)亦然,如果我们很专注虔诚的在念诵,就不会有负面的心态;如果只是机械式的进行宗教仪式,我们可能一边诵经,而心中却充满不好的感觉。
证得初果后,我们的心会比以前更敏锐,因此更能觉知贪与嗔的生起。当贪与嗔生起时,我们发现贪与嗔更令人烦恼。之前,几乎不会干扰我们的隐微的不善心境,现在变成大的干扰。事实上,这对我们的修行是一种激励。所以修行不只是在表面上应该有正当的行为,还需要不断净化我们的心。
等到时机成熟,才会从初果道心进入二果道心,通常这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过世俗生活的人,因为世俗的生活、心态、习俗和社会行为(conduct)与此相反,不支持这种修行,所以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
证得二果,我们有两件事必须牢记在心,也就是有关自我的正见与果心。此时,虽然没有第一次证得道心与果心时的大喜和解脱感,但我们仍需尽可能的使这种喜悦与解脱感生起。
另外,观察五盖的生起也很有帮助,看看哪个盖比较强,哪个盖已减弱。证得初果,五盖中的疑已经消失。五盖中的前两个盖是贪与嗔,我们要观察贪与嗔的生起;也要观察第三和第四个盖,即昏沉睡眠与掉悔。我们不断的问自己:「现在哪个盖最强?是如何生起的?」不断的观察五盖,才能减轻它的影响。当然,无论在修行的哪个阶段,我们都应该如此观察,同时必须了解五盖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有透过修行才能去除五盖。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的不净,也许就不会再责备他人。
预流者能觉知到这点,不会把五盖的生起归咎他人。他们观察身心的生灭现象时,发现并没有「我」在其中,所以没有人可以归咎。尚未证得初果的人很难做到这点,因为我们通常不想知道自己的负面情绪。
据说证得初果的圣者不会毁犯五戒,也就是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以及不饮酒和吸食麻醉物品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观察自己是否能受持五戒,而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
以上所说的都与省察智(reviewing knowledge)有关,省察智在退出禅那时特别有用,因为此时的心非常清净、清明,最有利于重温果心,重新省察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我们必须一再的审察,直到完全了解「自我」的虚幻不实,使我们不再珍惜自我为止。这不表示我们会自责或想去改变它,而是知道「自我」这概念是想出来的。我们必须观察一切事物和我们的感受,看看我们的心是否愿意放下这个由身心组合的自我,是否愿意彻底去除「自我」,没有任何保留,任何与「我」有关的念头是否会再生起,因为如果有自我,就会有不良的后果。在这个阶段,自我感仍会生起,会妨碍修行。和以前一样,我们可以让心寂止,可是我们试了许多次,心仍无法寂止。果真如此,我们必须去观察我们执着的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东西,经过分析后,我们仍不愿意放下那个正在体验(experience)的觉知者,也就是「自我」。
刚开始,修行的动力可以把我们带过河。为了重新体验解脱的境界,我们必须放下所有与「自我」有关的事物。如果仍执着人类的生活,无论是感官欲望、性欲,或其他事物,我们很难进步。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找出「是什么东西使我如此执着,不肯放下?」如此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执着某人,这种执着会使我们变得依赖和忧惧,因为那个人可能随时消失,我们的执着只会带来更多的苦。
如果我们执着某些欲望,我们会发现任何欲望的满足都是短暂的,没有多久,心又会再度感到空虚,欲望需要一再满足。这是我们观察我们的执着的方法,我们想了解实相,而有些人不愿意太深入,这当然没问题,在修行道上,如果我们已经站稳脚步,就一定会向前迈进,继续证得各阶段的观智。
证了初果后,凡是迈向下一步的圣者称为一来者,意指证得此果位的圣者,在今生生命结束后,只会再来欲界一次。证得初果及二果的圣者,都会将所证得的道智及果智带到下一生,所以这些人对我们大有助益,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可以教导我们。
证得二果后,贪与嗔会减弱,但并未根除。「嗔」会减弱为厌烦,「贪」会减弱为喜好(preference),二果圣者的心不会被贪嗔所动摇,因为厌烦与喜好只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心,比起嗔来,厌烦对心的影响时间较短,而厌烦与喜好比贪嗔要温和得多。证得二果的圣者会用省察智来观察,也会发现厌烦与喜好仍然会产生苦。
一来者(二果圣者)所经历的道心与初果相似,但并非相同,也很难用言语表达;接着会生起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果心。证得初果时,那种心神不宁的感觉不会在证得二果时生起。此时内心有完全解脱的感觉,通常不会流泪,可以说是大喜,虽然大喜不会立刻生起。心再度寂止,即无所有的境界,这种经验很真实。在这种境界中,身体、树木、房子、车子、道路、灌木和高山并非消失了,就相对层次而言,它们仍然存在,就绝对层次而言,它们只是一堆由能量聚合而成的分子,聚合又分散;它们聚合成某种形式,形成各种现象。无所有的境界就是:在一剎那间体验到一切事物变为碎片,而不再经历生起的境界。
在证得道心与果心前,我们必须先证得不同的内观智慧。首先知道我们是由身与心所组成,身与心并非一体,只是互相依存(这是名色分别智)。其次,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生起后必定会消失(这是生灭随观智)。接着,我们会观察到一切现象都会坏灭(这是坏灭随观智)。当我们看到坏灭的现象时,除非我们已经证得道心,否则可能会心生怖畏(这是怖畏现起智)。如果心生怖畏,就要向老师请教,并获得勇气。我们必须知道:修持内观智慧禅法,这种怖畏是修行的一个阶段,不是出了差错。在修习内观时,我们也了解身与心的因果关系,如我们在《布咤婆楼经》中所看到的,身体由四大组成,由食物所养,所以四大和食物是因,而身体是果,我们必须如此观察。
在修习内观智慧禅时,有了怖畏的体验后,又把它放下,此时,会迫切的去修行,并希望能解脱(这是欲解脱智)。接着,出离心与离欲使我们能证得道心,证得道心(道智)后,我们能如实的了知事物的真相。随之生起的果心(果智)使我们不再怀疑所经历的,而每一刻的果心会越来越强,之前的果心通常会在记忆中消失。所以我们对刚生起的果心会有最深的印象,因为它会带来大喜与解脱。
事实上,很少人能体证道心,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意外。因为大部份的人都受贪与嗔的影响,我们要经历两次的道心,才能使贪与嗔减弱。在去除贪与嗔之前,我们仍须不断的禅修。
证了二果后,我们还有两个阶段要完成。这两个阶段显然是最难的。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我,使贪与嗔完全消失。再经历一次道心后,贪与嗔将被根除,于是前五个「结」全部去除,也就是所谓的「五下分结」全部消失,此时,已证得三果,成为不还者,意指此生结束后,不会再回来人间。证得三果并不容易,即使证得三果仍有五个结需要断除,才能证得阿罗汉果,此时「自我」才完全根除。如果三果圣人于死前未能证得阿罗汉果,由于仍有色贪及无色贪,就会投生到净居天,在那里证得阿罗汉果,这是因为三果圣者仍有五上分结,仍有投生在无色界的欲望。
不还者还有我慢与痴(无明)两个结。此处的痴指内心深处非常隐微的自我感。「慢」并非指傲慢,而是指自我的「想象」(a “conceiving” of a self)。因为有这两个结,所以心仍会掉举,当然这种掉举与世俗的掉举截然不同,后者指心不断的追求外物来满足欲望。对不还者而言,由于隐微的自我感仍未消失,所以仍未完全脱离苦。修行到了这个阶段,要观察的心理活动变得非常隐微,那些比较粗的「盖」已经消失,而剩下的掉举也变得非常微细,一旦觉察到它的存在,就会立刻消失,所以三果圣者仍需继续修行。
欲证三果的二果圣者应以类似的方法修行,即观察前三个结(即身见、戒禁取见、疑),肯定它们已经消失,并观察贪与嗔,肯定贪与嗔已经变薄弱。二果圣者的「自我」远比三果圣者来得大。当我们观察自我时,会发现并没有「人」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感觉到有「人」在说话和反应,这是因为仍有某种程度的贪与嗔。因此我们要有正见,重新生起果心,并观察自我的虚幻不实。这种观察必须非常彻底和深入,因为证得不还果是极大的转变,所以必须一再的观察。这种观察不只是理智的观察,而是完全投入,放下一切,所有世俗的事物都要放下。尤其是身心中和「自我」有关的都要去观察。
此外,必须有极强的决心,那么(三果)道心就会生起,如以前一般,心又再度寂止,此时,没有任何念头;接着果心会生起。在三果道心生起前,由于心已经体验过两次的道心,所以这次没有强烈的感觉,而道心是很短的,而随之生起的果心只是一种认知,没有泪水和大喜,只有觉知和清明,以及解脱感:「啊,终于解脱了!」而不再有之前证果时的满足感,心也非常清楚仍有余结要断除。
不还者必须观察剩下的五个结,看看自己是否仍想投生在较高的天界。不还者有这种欲望,所以会希望一切都是愉快的和宜人的,也就是不想有任何的苦。当然这也是一般人的心态,而三果圣者不止于此。这种心态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希望能投生在只有快乐没有苦的无色界。这种强烈的感觉也要观察,而剩下的比较微细的「自我」也要观察。佛陀提醒弟子们要观察这欲望,因为投生在无色界的众生寿命很长,一旦投生到那里,就会有无数劫的寿命,所以有些天人以为自己的寿命是无限的。在人间,有许多苦来刺激我们修行,而三果圣者所投生的净居天就完全没有苦,所以要他们彻底解脱是很难的,所以佛陀说:这种欲望不利于修行。
不还者应更进一步去除剩下的五个结,因为这是应该做的,而不还者也的确感到剩下的五个结中的掉举仍然是苦;而想投生在较高的天界的欲望虽然非常小,也是苦,而这隐微的,尚未断除的「自我」也是苦。
修行的最后一步和之前的大致一样,不同的是,心决定要让这身心所构成的人完全消失。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留住我们,应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没有甚么事需要做。一如以往,道心是无法用语言文字形容的。四果道心的专有名词是无生(non- occurrence),因为「不受后有」,不再投生,所以称为「无生」。
随之生起的果心就有此感受。佛陀说未曾经历过此境界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境界非常可怖。事实上,完全的止息会带来大喜。这种经验很难形容,就像跌入云端,接着就在云中消失一般。证果后,一切已不复旧观,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影响阿罗汉的心。就像和小孩子玩耍般,我们会对小孩子很友善,乐于和孩子们相处,当和他们玩积木时,也会帮他们堆砌城堡,然而我们会对这游戏认真吗?如果有人不小心踩到积木,把城堡毁了,孩子们或许会大叫,而我们不会。当然我们也在帮人们建筑城堡,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告诉他们不值得花时间去建这些城堡,不要太认真。我认为这个譬喻将证果后的心境说得非常清楚。证得阿罗汉的圣者,将「自我」彻底根除,已究竟解脱,可以随时回到苦完全止息的大喜。
经中记载佛陀证得涅盘后,安住其中,体验涅盘之乐达七天之久,才决定将所体验到的和世人分享。这种自我感的完全去除是修行的极致。正如经中所说的,这位年轻、出身良好的年轻人离家出家,修行证果,「所应做已做,不受后有」,最后,甚么事情也没有。 三学、七清净与十六观智三学七清净十六观智
戒学一.戒清净
定学二.心清净
慧学三.见清净1.名色分别智
四.度疑清净2.缘摄受智
五.道非道智见清净3.思惟智
4.生灭随观智
六.行道智见清净 4.生灭随观智 5.坏灭随观智 6.怖畏现起智 7.过患随观智 8.厌离随观智 9.欲解脱智 10.审查随观智 11.行舍智 12.随顺智 13.种姓智(第六、第七 清净之间)七.智见清净14.道智 15.果智 16.返照智
布咤婆楼经
1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与苦行外道众三百人,住末梨园中,提陀迦树环繞之大讲堂。
2尔时世尊,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然于其时,世尊念言:「于舍卫城游行乞食,为时尚早,宁可往旁末梨园中,提陀迦树环繞之大讲堂。」3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与诸多侍众共坐一处,大声喧嚷,互相詈骂,耽于种种无益议论,即论王、论盗、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论饮、论衣、论床、论鬘、论香、论亲戚、论乘具、论部落、论村庄、论都市、论乡间、论妇女、论勇士、论市街、论琐事、论亡灵、论余杂事、论水陆起源,及论斯有斯无等。
4尔时布咤婆楼苦行外道遥见世尊自彼方来,即令其众,静默毋哗,曰:「诸士,肃静勿作声。沙门瞿昙来矣。彼爱沈默,并赞叹沈默。盖知吾等会众沈默,当觉来访之不虚也。」彼等苦行外道,闻是言已,众皆沈默。
5世尊行近布咤婆楼所。布咤婆楼语世尊曰:「善来世尊,吾等欢迎世尊。世尊久不来此。请坐世尊。此座之设,为世尊也。」世尊就所设座而坐。布咤婆楼别取低座,坐于一旁。世尊问布咤婆楼曰:「布咤婆楼,今汝等集此,为何论议?而汝等论议何故中止耶?」6布咤婆楼闻是言已,答世尊曰:「世尊,吾等集此,所欲论者,可(且)置之。因此等论,日后易得也。世尊,曩者多有外道沙门婆罗门,集此论议场所,就增上想灭,发论议曰:『增上想灭,云何而起耶?』时有一类,作是说言:『人人皆以无因无缘而想生,无因无缘而想灭。生时即有,灭时则无想。』斯一类者,以如是说增上想灭。余者,作是说言:『不然,吾友,想实人我也。夫人我,有来有去。来时即有想,去时即无想。』斯类者,以如是说增上想灭。复有余者,作是言:『不然。实有沙门、婆罗门,具大神通、大威力。其于人也,移想而来,掣想而去。移来则有想,掣去则无想。』斯类者,以如是说增上想灭。世尊,尔时,我心生念。念言世尊:『呜乎世尊,精通此法。倘于此时,世尊在者,倘于斯时,善逝在者。实因世尊熟知增上想灭者也。世尊,何者是增上想灭?』」7「布咤婆楼,彼婆罗门言『人人皆以无因无缘而想生,无因无缘而想灭。』误矣!所以者何,布咤婆楼,有因有缘,人之想生;有因有缘,人之想灭。由于修习而想生,由于修习而他想灭。」世尊说言:「云何修习?布咤婆楼,今者如来出现于世,如来是应供、等正觉、乃至身业、语业,清净具足,营净生活,具足戒行,诸根之门,悉为守护。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满足。 如来出现于世,是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来于此世界、天界、魔界、梵天界、于此大众、诸天、世人、沙门、婆罗门、自身证悟,而为说示。如来宣说教法,初善、中善、终亦善,文义具足,示教梵行,完全清净,无与伦比。 若长者,若长者子,若生于余种姓者,听受如来教法,彼等听受已,信仰如来,得信仰故,如是思惟:「障碍哉尘劳家居。自在哉出家生活。专修梵行,完全清净,耀如螺钿,若处居家,殊非易事。今我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离家出家。」乃于后时,弃捐财业,舍去亲族,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离家出家。 如是出家者,以波罗提木叉禁制,而住持戒。精勤正行,虽于小罪亦见怖畏,受持学处而自修学。身业、语业,清净具足,营净生活,具足戒行;诸根之门,悉为守护,具足正念正知,自知满足。 布咤婆楼,比丘云何具足戒行?布咤婆楼,今有比丘,舍杀离杀,不用刀杖,怀惭愧心,充满慈悲,利益一切生类有情,而住悲悯,此为比丘戒行一分。复次,或有沙门、婆罗门,为世所敬,食他信施,然于诸无益徒劳之行,若许愿还愿,乃至给树根,施药料,除药料等。以此等行,邪命自活,今于是事,皆悉舍离。此亦为比丘戒行一分。
8布咤婆楼,比丘如是戒行具足,因戒制御,故在在处处,皆无怖畏。如是乃至彼具足圣戒聚,内心无垢,纯净安乐。布咤婆楼,比丘如是具足戒行。
9布咤婆楼,比丘云何守护诸根之门。布咤婆楼,今有比丘,以眼见色时,不取总相,亦不取别相。彼若无所抑制,则其眼根,随生贪爱、忧悲、过恶与不净法。彼御此眼根,以护眼根,令其眼根,归于制御;以耳闻声时,亦复如是;以鼻嗅香时,亦复如是;以舌尝味时,亦复如是;以身触所触时,亦复如是;乃至以意知法(境)时,不取总相,亦不取别相。彼若无所抑制,则其意根,随生贪爱、忧悲、过恶与不净法。彼御此意根,以护意根,令其意根归于制御。此诸圣根,具足制御,内心无垢,纯净安乐。布咤婆楼,比丘如是守护诸根之门。 复次,布咤婆楼,比丘云何具足正念正知?今有比丘,若进若退,悉以正知;直视、周视,悉以正知。若屈伸手足,若执持衣钵,若饮食咀嚼,若大小便利,若行住坐卧,若觉醒语默,于一切时,悉以正智。布咤婆楼,比丘如是具足正念正知。 复次,布咤婆楼,比丘云何自知满足?今有比丘,以衣保身,以食养体,自知满足。任往何处,持与俱行,如有翼鸟,任飞何处,羽翼随身。此比丘亦复如是,以衣保身,以食养体,自知满足,任往何处,持与俱行,布咤婆楼,比丘如是自知满足。 具足如此圣戒聚,圣诸根制御,圣正念正知,圣满足比丘,或在静处,或在树下,或在山谷,或在岩窟,或在冢间,或在林薮,或在露野地,或在槁堆,离世闲居,彼受施食还,食已,结跏趺座,端身安住于深正念。 彼于世间,弃除贪欲,住无贪欲心,离去贪欲,令心净化,弃除害心,弃除嗔恚,住不害心,普为利益慈愍一切生类有情。离去害心,离嗔恚,令心净化。弃除昏沉,弃除睡眠,离去惛睡,系想分明,正念正知。离去昏睡,令心净化,弃除掉举,及以恶作,住心轻安,内心寂静。离去掉举,及以恶作,令心净化,弃除疑惑,住离疑惑,而于净法无有疑惑。离去疑惑,令心净化。
10舍此五盖,观自身者,便生欢喜。欢喜者生喜,怀喜者身安稳,身安稳便觉乐,乐则心入三昧。彼离诸欲,离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入住初禅。因此先灭欲想,是时生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彼已离生喜乐,润渍其身,周遍盈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离生喜乐。因此先灭欲想,是时生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 譬如善巧浴仆,或其弟子,于盥浴器,而撒澡豆,以水渍调,澡豆受润,因润散碎,内外俱润,以至周遍,无不遍满。比丘亦复如是,离生喜乐,润泽其身,周遍盈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离生喜乐。因此先灭欲想,是时生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11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灭除寻伺,内心静安,得心一境相,无寻无伺,定生喜乐,入第二禅。是时先灭离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定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定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定生喜乐,润泽其身,周遍盈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无喜之乐。譬如有水涌出深泉,其水不从东来,不从西来,不从北来,不从南来,而时时予以骤雨。由此深泉涌出凉水,以此凉水,润渍深泉,周遍盈溢,且复充满全泉之水,无不普洽。比丘如是,定生喜乐,润渍其身,周遍盈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定生喜乐。
12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离喜住舍,正念正知,身受快乐,如诸圣说,『舍念乐住。』入第三禅。是时先灭定生喜乐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舍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舍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譬如青红白莲,一一莲池,是莲皆生水中,皆长水中,皆浸水中,为水所养,由顶至根,以水润渍,周遍盈溢,且复充满,全身到处,无不遍满无喜之乐。
13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舍乐离苦,先灭忧喜,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禅。是时先灭舍乐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不苦不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不苦不乐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譬如有人,由顶至踵,以白净衣被覆,全身到处惟白净衣。比丘亦复如是,以纯净心充满其身,全身到处惟纯净心,周洽普遍。如是心寂静纯净,无有烦恼,离随烦恼,柔然将动,恒安住于不动相中,尔时比丘,以心倾注于智见。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四大种成,父母所生,粥饭长养,为无常、破坏、粉碎、断绝、坏灭之法,又我之识依存于此,与此关联。」 譬如琉璃宝珠,美丽优雅,八面玲珑,磨治莹明,清澄无浊,具一切美相,以索贯之,索深青色,若深黄色,若赤红色,若纯白色,若淡黄色,有目之士,置掌而观,当如是观此琉璃之相。比丘如是,心寂静纯净,…尔时比丘,以心倾注于智见。彼知是事:我身由色成…我之识依存于此,与此关联。
14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超出所有色想,灭障碍想,不忆异想,故达空是无边之空无边处,因此先灭此想,同时生空无处乐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惟有空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今有沙门或婆罗门,作如是论,作如是见:「此我为有色,四大所成,父母所生,而身坏时,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 复有余者于此作是说言:「汝言之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是天而有色,属于欲界,养于段食,汝不知见,予知见之。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 复有余者于此作是说言:「汝言之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是天而有色,且意所成,肢节具足,诸养无阙,汝不知见,予知见之。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 复有余者于此作是说言:「汝言之我,斯我实存,予决不谓,斯我不存,然而此我,非全断灭。犹有他我,超出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忆异想,故达空是无边之空无边处。汝不知见,予知见之。此我身坏,断灭消失,死后无存。于是此我,全归断灭。
15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超出所有空无边处,达识是无边之边处,因此先灭空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无所有处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识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16世尊复言:「布咤婆楼,复有比丘,超出所有识无边处,达所有皆无之无所有处,因此先灭识无边处之微妙真实想,同时生无所有处之微妙真实想,以此之故,彼于是时,具有无所有处之微妙真实想,如是由修习故想生,由修习故他想灭,此由于修习也。
17布咤婆楼,以比丘有独特之想,彼便由前至后,次第以至想之极致,处此想之极致时,彼作是念:「思虑之事,于我为恶;不思虑事,于我为善。设我仍有思虑意欲,我之此想虽得消灭,而余粗想将复再生。我今宁可不为思虑,不起意欲。」彼便不为思虑,不起意欲。不为思虑不起意欲已,其想即灭,余想不生,而彼想灭。布咤婆楼,如是次第以至增上想灭智定。
18「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汝曾闻如斯次第增上想灭智定否?」否也,世尊,今吾唯知世尊所说,谓:「以比丘有独特之想,彼便由前至后,次第以至想之极致,处此想之极致时,彼作是念:『思虑之事,于我为恶;不思虑事,于我为善。设我仍有思虑意欲,我之此想虽得消灭,而余粗想,将复再生。我今宁可不为思虑,不起意欲。』彼便不为思虑,不起意欲。不为思虑不起意欲已,其想即灭,余想不生,而彼想灭。布咤婆楼,如是次第以增上想灭智定。」布咤婆楼,实如是也。
19「世尊,世尊说示想之极致,为一为多耶?」,「布咤婆楼,吾所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如是世尊,云何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耶?」,「布咤婆楼,实如是如是而想灭,遂如是如是现想之极致。布咤婆楼,故吾说示想之极致,亦一亦多。」20「世尊,先有想生,然后智生耶?先有智生,然后想生耶?抑智与想非前非后而生耶?」布咤婆楼,先有想生,然后智生;实由想生,而智生起,是以人人皆悉自知:「实由此缘故,于吾生智慧。」布咤婆楼,可知依此理趣,先生想,后生智,由想生故有智生起。
21「世尊,想即人我耶,抑想与我为异耶?」布咤婆楼,汝以何者为我耶?「世尊,吾自思惟,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布咤婆楼,汝之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设若真实,布咤婆楼,则汝想与我,实非一物。布咤婆楼,由此差别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咤婆楼,如是粗我有形,四大所成,段食所养。但于此人,犹有一想生,他想灭。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实非一。
22「世尊,吾以我为意所成,肢节具足,诸根圆满。」布咤婆楼,汝之我为意之所成。肢节具足,诸根圆满。设若真实,布咤婆楼,则汝想与我,实非一物。布咤婆楼,由此差别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咤婆楼,如是我为意所成,肢节具足,诸根圆满。但于此人,犹有一想生,他想灭。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实非一也。
23「世尊,吾以我为无形,而想所成。」布咤婆楼,汝之我为无形,而想所成。设若真实,布咤婆楼,则汝想与我,实非一物。布咤婆楼,由此差别智,可得而知,想我非一,布咤婆楼,如是我为无形,而想所成。但于此人,犹有一想生,他想灭。布咤婆楼,由此差别,可得而知,想我实非一。
24「复次世尊,人我即为想耶?抑想与我为异耶?斯义吾可得知不?」布咤婆楼,我与想为同一耶?抑想与我为各异耶?汝欲知此,甚难甚难。以汝依他宗见,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研究为归,以他宗之行持为旨故。
25世尊,若吾依他宗见,有他宗信仰,持他宗所期,以他宗之研究为归,以他宗之行持为旨者,故此想即为人我耶?抑我与想为各异耶?知之甚难,如是世尊。 复欲请问,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 布咤婆楼,世界常住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此为吾所不记。 如是世尊,此世界无常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世界无常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此为吾所不记。 复次世尊,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世界有限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此为吾所不记。 复次世尊,世界无限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26复次世尊,此命与身为一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复次世尊,此命与身各异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27如是世尊,如来死后存在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如是世尊,如来死后不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如是世尊,如来死后亦存在亦不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如是世尊,如来死后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唯此真实而余者为虚妄耶?布咤婆楼,此为吾所不记。
28「世尊,凡此等等,世尊何故判为不记耶?」布咤婆楼,此不与义合,不与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离,非趣离欲,非趣止灭,非趣寂静,非趣证悟,非趣正觉,非趣涅盘,是故判为不记。
29「如是世尊,世尊所记为何?」布咤婆楼,「此是苦」,实吾所记者也。布咤婆楼,「此是苦集」,实吾所记者也。布咤婆楼,「此是苦灭」,实吾所记者也。布咤婆楼,「此是趣苦灭之道」,实吾所记者也。
30「然世尊所记,为何故耶?」布咤婆楼,此实合义合法,是根本梵行,是趣出离,是趣离欲,是趣止灭,是趣寂静,是趣证悟,是趣正觉,是趣涅盘,故为吾所记。「诚然世尊,诚然善逝。世尊请便,今正是时。」于是世尊起座而去。
31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等皆向布咤婆楼苦行外道讥诮曰:「布咤婆楼,于沙门瞿昙所说,作如是赞叹:诚然世尊,诚然善逝。然于「世间常住耶,世界无常耶,「世界无限耶,世界有限耶,命与身为一耶,命与身各异耶,如来死后存在耶,如来死后不存在耶,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等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布咤婆楼闻是言已,告彼等苦行外道曰:「诸士,世间常住耶乃至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固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但沙门瞿昙所说之道,如实真正,真如,住法合法,沙门瞿昙,如是善说,如实真正,真如,住法合法之道时,理智如吾者,何由不赞叹此善说法者耶?
32后二三日,象首舍利弗与布咤婆楼诣世尊所,象首舍利弗礼敬世尊,坐于一面,布咤婆楼亦亲礼世尊,殷勤问讯,就一面坐。布咤婆楼白世尊言:「世尊,世尊去未久,苦行外道等,皆向吾作讥诮曰:『布咤婆楼,于沙门瞿昙所说,作如是赞叹:诚然世尊,诚然善逝。然于世间常住耶,乃至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等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世尊,吾闻是言已,答彼等苦行外道曰:『诸士,世间常住耶,乃至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凡此诸问,吾固不见沙门瞿昙确示一法。然沙门瞿昙所说之道,如实真正,真如,住法合法,沙门瞿昙,如是善说如实真正真如,住法合法之道时,理智如吾者,何由不赞叹此善说法者耶。』」33布咤婆楼,彼等一切苦行外道,皆悉盲目,为无眼子,而于其中,唯汝一人具眼士也。布咤婆楼,我所说法,有决定记,不决定记。布咤婆楼,云何名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盖谓「世界常住耶」者是也,布咤婆楼,此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复次,布咤婆楼谓「世界无常耶」者是也,此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布咤婆楼,谓「世界有限耶,乃至如来死后亦存在亦非不存在耶」者是也,此亦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 布咤婆楼,何故此等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布咤婆楼,以此等不与义合,不与法合,非根本梵行,非趣出离,乃至非趣涅盘故也,是故此等为我所说法,不决定记。 布咤婆楼,云何名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布咤婆楼,「此是苦」,实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布咤婆楼,「此是苦集」,实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布咤婆楼,「此是苦灭」,实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布咤婆楼,「此是趣苦灭之道」,实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 布咤婆楼,何故此等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布咤婆楼,以此等与义合,与法合,是根本梵行,是趣出离,乃至是趣涅盘故也。是故此等,为我所说法之决定记。
34布咤婆楼,或有一类沙门婆罗门,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我访彼等,如是问曰:「诸友,汝等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真实不耶?」彼等闻是言,报我曰:「然。」我又问曰:「诸友一安乐之世界,汝等实知实见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我又问曰:「诸友,汝等于一夜或一日,于半夜或半日,亦曾审知有一向安乐之我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我又问曰:「诸友,趋于一向安乐世界,惟此道可实现,惟此路得通达。汝等曾了知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我又问曰:「诸友,生彼世界一向安乐安乐之天神曰:『尊主若欲实现一向安乐世间,当行善业,当行正道,当步正道,所以者何?吾等所行正尔,故得生于一向安乐世界。』汝等曾闻其说示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合正理否?
35譬如有人,作如是言:「吾于此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余人若问:「吾友,汝于此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则汝当知,国中所谓第一美女,属剎帝利族耶,婆罗门族耶,吠舍耶,抑首陀罗耶。」彼闻是言,答曰:「不知。」 又问彼曰:「吾友,汝于国中,求交且爱第一美女,则汝当知,在此国中,第一美女,名何姓何,彼女身躯,长耶短耶?适中耶?彼女皮肤,青黑耶?纯黑耶?黄金色耶?彼女所住,村落乡镇耶?抑城市耶?」彼闻是问,答曰:「不知。」 又问彼曰:「吾友,汝求交且爱者,汝竟不知其人,不见其人耶!」彼闻是问,答曰:「唯然。」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不?世尊,此人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36布咤婆楼,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我访彼等,如是问曰:「诸友,汝等谓我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真实不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 我又问曰:「诸友,汝等于一夜或一日,于半夜或半日,亦曾审知一向安乐之我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唯然。」 我又问曰:「诸友,趋于一向安乐世界,惟此道可实现,惟此路得通达。汝等曾了知耶?」彼等闻是问,答我言:「不也。」 我又问曰:「诸友,生彼世界一向安乐之天神曰:『尊主,若实现一向安乐世界,当行善业,当行正道,所以者何?吾等行此,故得生于一向安乐世界。』汝等曾闻其说示耶?」彼闻是问,答我言:「不也。」 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不?世尊,此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37布咤婆楼,例如有人,于四衢道处,欲树立一梯,以登殿堂,余人问彼曰:「今者吾君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东方耶?在西方耶?在北方耶?抑南方耶?其堂高耶?低耶?抑适中耶?君知之耶?」彼于此问答曰:「不知。」 余人又问:「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君竟不知不见耶?」彼于此问,答曰:「唯然。」 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否?世尊,此人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38布咤婆楼,沙门婆罗门,亦复如是,谓「我于死后,一向安乐,亦且无病。」作如是言,有如是见。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合正理否?世尊,彼等沙门婆罗门所说,实不合正理也。
39布咤婆楼,实有三种我得,即粗我得,意所成我得,无形我得。布咤婆楼,何者是粗我得耶?有形而四大所成,段食所养者,粗我得也。何者是意所成我得耶?有形而肢节具足,诸根圆满者,意所成我得也。何者是无形我得耶?无形之想所成者,无形我得也。
40布咤婆楼,我之说法,实欲使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达,至于安住。布咤婆楼,汝意或谓:「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欲自证达,至于安住,然而有情犹住苦中。」 布咤婆楼,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能自证达,而自安住,是则愉悦欢喜,成就轻安,又得正念正知,住于安乐。
41布咤婆楼,我之说法,实为欲使永断意所成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达,至于安住。 布咤婆楼,汝意或谓:「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欲自证达,至于安住,然而有情犹住苦中。」 布咤婆楼,勿作是念,所以者何,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能自证达,而自安住,是则愉悦欢喜,成就轻安,又得正念正知,住于安乐。
42布咤婆楼,我之说法,实欲使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
43布咤婆楼,又若有人,向我问曰:「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耶?」于如是问,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欲使永断粗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44布咤婆楼,又若有人,向我问曰:「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意所成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耶?」于如是问,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欲使永断意所成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45布咤婆楼,又若有人,向我问曰:「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耶?」于如是问,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欲使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 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我之所说,合正理不?世尊,世尊所说,实合正理也。
46布咤婆楼,犹如树立一梯于殿堂下,欲登一殿堂,余人问彼曰:「今者吾友欲立一梯,以登殿堂,而此殿堂在东方耶?在西方耶?在南方耶?抑北方耶?高耶?低耶?抑适中耶?君知之耶?」彼答问言:「我之立梯于殿堂下,为欲如是以登殿堂。」 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此人所说合正理否?世尊,彼之所说,实合正理也。
47布咤婆楼,此亦如是,设若有人,向我问言:「尊者,汝之说法,云何永断粗我得?复次,汝之说法,云何永断意所成我得云云?复次,汝之说法,云何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于现法中,智慧充广,自身证达,至安住耶?」于如是我当答曰:「吾友,我之说法,如是永断无形我得,依之随入,断离染污法,增长清净法,如是乃至住于安乐。」布咤婆楼,于汝意云何?我之所说,合正理不?世尊,世尊所说,实合正理也。
48时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世尊,粗我得存在时,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无形我得之存在亦虚。正于尔时,唯粗我得之存在为实耶?
世尊,意所成我得存在时,粗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无形我得之存在亦虚。正于尔时,唯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为实耶 ?
世尊,无形我得存在时,粗我得之存在为虚,而意所成我得之存在亦虚。正于尔时,唯无形我得之存在为实耶?
49象首,粗我得存在时,唯名为粗我得,决不名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 象首,意所成我得存在时,唯名为意所成我得,决不名粗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 象首,无形我得存在时,唯名为无形我得,决不名粗我得,亦不名为意所成我得。 象首,设若有人向汝问言:「汝曾存于过去世,汝非已有耶?汝将存于未来世,汝非当有耶?汝存于现在,汝非今有耶?」象首,有是问者,汝云何答? 世尊,设若有人,向我问言:「汝曾存于过去世,汝非已有耶?汝将存于未来世,汝非当有耶?汝存于现在,汝非今有耶?」世尊,有是问者,我当答言:「我曾存于过去世,我曾已有;我将存于未来世,我为当有;我存于现在,我为今有。」世尊,于如是问者,我当如是答。
50象首,又若问汝:「汝有过去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未来我得为虚,现在我得亦为虚耶?复次,汝有未来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我得为虚,现在我得亦虚耶?复次,汝有现在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我得为虚,未来我得亦虚耶?」象首,有是问者,汝云何答? 世尊,若问我言,「汝有过去我得时,如是乃至汝有现在我得时,唯汝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未来者亦虚耶?」 世尊,有是问者,我当答言:「有过去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未来者为虚,现在者亦虚也。复次,我有未来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现在者亦虚也。复次,我有现在我得时,唯我之此我得为实,而过去者为虚,未来者亦虚也。」于如是问者,我当如是答。
51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时,决不名为意所成我得,亦不名为无形我得,唯名为粗我得也。象首,意所成我得存时,乃至象首,无形我得存时,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意所成我得,唯名为无形我得也。
52象首,譬如由牛有乳,乳变为酪,酪为生酥,生酥为熟酥,熟酥为醍醐,当有乳时,唯名为乳,决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不名醍醐。当有酪时,乃至有酥时,乃至有醍醐时,唯名醍醐,决不名乳,亦不名酪,不名生酥,不名熟酥。
53象首,此亦如是,粗我得存时,乃至意所成我得存时,乃至无形我得存时,决不名为粗我得,亦不名为意所成我得,唯名为无形我得也。象首,凡此等等,为世间共相,世间言语,世间名称,世间记述法,如来用之,正当者也。
54世尊如是说已,布咤婆楼苦行外道曰:「伟哉世尊,大哉世尊,犹如使倒者得起,闭者得开,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灯,有目得视。世尊以无数方便,说示教法,亦复如是。世尊,我今归依佛陀,归依法,归依僧众。唯愿世尊,听摄受我,自今已后,尽寿归依,为优婆塞。」55象首舍利弗白世尊言:「伟哉世尊,大哉世尊,犹如使倒者得起,闭者得开,迷途者示之以道。冥室燃灯,有目得视。世尊以无数方便,说示教法,亦复如是。世尊,我今归依佛陀,归依法,归依僧众。唯愿世尊,许我等于世尊所,得出家受具戒。」56于是,象首舍利弗,于世尊处,出家受具戒,受具戒后,尊者象首舍利弗,即独处,不放逸,殷勤专念,精勤止住。为良家子出家所求最上梵行之究竟道,彼为时未久,即于现在,自身作证,自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尊者象首舍利弗,成阿罗汉。
修习慈心
(Metta Bhavana)
1. 愿我无怨,无瞋,无忧,
愿我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2. 愿我的父母、师长、亲人、同参道友,无怨, 无瞋,无忧,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3. 愿在此寺的所有禅修者,无怨,无瞋,无忧,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4. 愿在此寺的所有比丘、沙弥、优婆塞和优婆夷,无怨,无瞋,无忧,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5. 愿四事护法众,无怨,无瞋,无忧,
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6. 愿此精舍,此居所,此寺院的护法诸天,无怨,无瞋,无忧,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7. 愿一切有情众生,无怨,无瞋,无忧,
愿他们守护自己,住于安乐。
作者简介
作者艾雅.柯玛(Ayya Khama)于1923年生于德国的犹太家庭。1938年与其他两百位儿童逃离德国,被送往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她的父母亲则到了中国。两年后,艾雅.柯玛到上海与父母团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家被关在日本人的战犯营,父亲在狱中去世。
之后,美国解放了战犯营,四年后,艾雅.柯玛移民美国,并育有子女各一,现在则有四个孙子。艾雅.柯玛于1960年至1964年间,与夫婿和儿子四处游历,足迹遍及喜玛拉雅山区的国度,而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禅修。十年后,艾雅.柯玛开始在欧洲、美国及澳洲教导禅修。
1978年,艾雅.柯玛在澳洲.雪梨附近成立了上座部森林道场。1979年在斯里兰卡,作者由大长老那罗达(Narada Mahathera)亲证剃度出家,法名为Khema,意为安稳;Ayya是值得尊敬的意思。在斯里兰卡的首都可伦坡,艾雅.柯玛成立了国际佛教徒妇女中心(International Buddhist Women’s Center),做为斯里兰卡出家女众的训练中心。另外还有专为女众闭关或剃度的尼众岛屿(Parappuduwa Nuns’ Island)。
1987年,艾雅.柯玛举办佛教史上第一届的国际佛教尼众会议,由达赖喇嘛担任主题演讲人。并成立一个世界性的佛教妇女组织-释迦儿女(Sakyadhita)。同年五月,成为第一位受邀到联合国发表有关佛教议题的演讲人。于1989年创立的德国Buddhist -Haus佛教团体,奉她为精神导师。1997年六月,艾雅.柯玛创立了德国的第一座佛教森林道场-慈心精舍(Metta Vihara),并第一次在此以德语举行剃度典礼。1997年十一月二日,艾雅.柯玛在德国圆寂。
艾雅.柯玛写了二十五本以上有关禅修和佛教教理的书,并以英文和德文弘扬佛法,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包括《缘起性空的世界》、《坚若盘石》、《何来有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你》等书。
愿以此法施功德,灭尽诸烦恼;
愿以此法施功德,成为涅盘因;
愿以此法施功德,与众生分享。
愿 一切众生安乐(慈),
愿 帮助众生离苦(悲),
愿 乐见众生成就(喜),
愿 待人冤亲平等(舍)。
译者:果儒
校对:慈迦、何彩熙
流通处:
◎慈善精舍(果道法师)
台北县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37巷17弄9号5楼
电话:(02)2648-6948
◎中平精舍(果儒法师)
32444桃园县平镇市新荣路71号(新势国小旁)⊕法雨道场(明德法师)
嘉义县中埔乡同仁村柚仔宅50~6号
电话:(05)2530029
⊕耿欣印刷有限公司
(02)2225-4005
初版:西元2010年5月 恭印3,00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