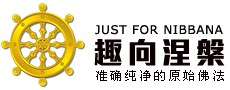滋养根柢
[中译]良稹
Nourishing the Roots
by Bhikkhu Bodhi
佛陀教导的灵性修持之道,是一个自我转化与自我超越、最终从苦中彻底解脱的双重过程。自我转化的过程要求弃绝非善巧心性,代之以利己利人的纯净心性; 而自我超越的过程,则是专注我们平常视为我与属我的身心过程,洞见其非我本质,由此弃绝自我中心之见。当这个双重过程达到顶点时苦被止息,这是因为随着智慧的觉醒,苦的本源——由无明支持的渴求——自此消失,不更复生。
由于非善巧倾向与自私性执取乃是来自深埋于内心最底层的种子,为了灭除这些苦痛的根源,培育如实的解脱洞见,佛陀以次第训练的方式解说他的教导。佛教修行之道需要渐次修练与逐步成就。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树木等生命形式一般,有机地展开; 它又如阶梯,每阶以下阶为必要的立足点,自然地引升上阶。这个次第修练过程主要阶段有三: 戒德的修持、定力的修持、智慧的修持。我们若把整个佛教修证比作一株树,则信念为其种子,因为正是信念提供了修道的原始动力,又是信念滋养着它的每一阶段。戒德为其根柢,因为正是戒德,如树根为大树确立基地,也为我们的灵性追求提供了基地。定力为其树干,它是力量、不移、稳定的象征。智慧为其分枝,从中结生出觉醒之花与解脱之果。
修行道的活力,一如树的活力,有赖于健康的根柢。正如根弱、浅植之树难以蓬勃生长,矮矬、枯萎、无果,灵修生活无强壮的根柢,生长亦将受矬,难以证果。修道中若期望高度成就,以善育根柢为起点至关重要,否则果报将会是失望、幻灭、甚至危险。圣道的根柢乃是sila的成分,也就是戒德的要素。它们构成了禅定的基础,由此出发引生一切智慧与高等成就。
不过,我们说戒德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其意并非如保守佛教圈内常常相信的那样,非戒德圆满不可开始禅修。这等规定使禅修几不可能,因为正是禅修过程所培育的念住、定力与智慧,带来了戒德的逐步净化。不过我们说戒德为修持之根柢,确实意味着,禅修的成就潜力有赖于戒德的纯度。假若我们的戒德根柢弱小,我们的禅修也将同样弱小。假若我们的行为与端正操行的基本原则反复冲突,那么禅定对调御心智的尝试,也将自取失败,因为那些行为的源泉,正是禅修意欲灭除的同一堆垢染心态。
只有当我们以正业的无咎原则为本,获得可靠的滋养,禅定的内在努力才有可能发展、成就。以正确的操行准则为基础,戒德的根柢将生起定力的主干,入定之心引生智慧的分枝,由智慧的分枝结生觉悟的花果,最终从结缚中彻底解脱。因此,正如一位善巧的园丁在植树时先滋养根柢,真诚的求悟者在起步时当照料他的修行根柢——那就是,他的戒德。
巴利语sila [戒德]原意仅指操行。不过在佛教灵性修持的背景下,该词特指一类操行,即正善操行,并且在引申意义上,指这类操行所代表的良好品德。因此sila既指有道德的行为——即为道德准则统辖的一套习惯,也指道德的德性——即常持这些准则意欲培育的内在素养。
这两层意义对理解戒德在佛教修行系统中的位置至关重要。戒德的前一种内涵,指身与语不逾越主导道德生活的基本戒律。这是行动与言辞意义上的道德纪律,以抑制欲藉身语渠道流出的不道德冲动为开端,发展成与端正操行原则的习惯性同步。不过,戒德的全副内涵未止于外在行为的控制,该词另有一重更深刻、更趋心理性的意义。在这第二重意义上,戒德是道德纯净度,即以道德原则持续规范人生所达到的内在品德的净化。戒德的这个层面强调的是行为的主观与动机。它的视向,非是外显的动作本身,而是引生良好操行的心的正态。
如此审视戒德,揭示其双维性质: 外在维度由操行的净化构成,内在维度由品德的净化构成。不过在佛陀的教导之中,内外体验的这两个维度,并非是相互分裂、相互隔离的两个自足领域。它们被认为是单一体的两个侧面、统一场的互补两极,相互映射,相互关联,以各自的影响潜力相互渗透。从佛教立场上看,身与语所作的种种行动[业],并非是某个独立灵性精髓的众多可卸附件,而是其背后作为激活源头的种种心态的具体示现。 反过来,种种心态,也并未封存于一个纯粹为精神性的隔离体内,而是随着场景的运作,从意识的源泉中升起、外溢,透过身、语、意的渠道,进入有关人际事件的世界。从行动,我们可以推断心态,从心态,我们可以预测可能的行动轨迹。两者关系之契合,如乐坛上的乐谱与它所指挥的演奏。
由于两个领域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有德的操行与品格的纯净以微妙复杂的关系相互契合。戒德净化的完成,要求这两个侧面都达到净化: 一方面,身与语的行为必须与道德理想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心性必须洗涤杂染,直至彻底清净。无后者,前者不充分,无前者,后者不可能。两者之间,从灵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内在侧面更为重要,因为身业与语业主要藉表达相应的心理素养得其伦理意义。不过在灵性修持的进阶中,道德戒律先行。因为修练之初,品德的净化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理念,非是一个可作为起点的现实。
根据佛教的缘起法,任何给定状态的实现,只有透过造就它的适当因缘才有可能,这既适用于身与心的自然现象,也适用于修练的各个阶段性成就。无始以来,意识的连续流一直被贪、嗔、痴的非善巧根性所败坏; 这些杂染正是我们绝大多数想法的起源、是我们习性的根基、是我们对他人与世界的行为与大体倾向的源泉。单凭意志一举祛除这些垢病,达到灵性圆满的顶峰,几乎是不可能的。灵修的实用系统,必须从人性原材料着手,既不可只满足于对人类优秀典范的推想,也不可强求成就却不给予实现之手段。
佛陀使他的教导立足于以下主旨: 以正确的方式,我们有能力改变自我。我们不会永远背着那付积习的重担,反之,借着自身的努力,必能摆脱这一切倾向,证得彻底的清净、自由。在正见的背景之下,具备了适当的手段,我们能够大幅度地改变意识的活动,从自己内心那块似乎不可变更的东西出发,塑造起新的状态。
这条道的第一步乃是净化品德,佛陀以遵守戒德即调控身语操行的一套戒律,作为重塑品德的有效手段。换言之,以道德纪律意义上的戒德为手段,引生道德德性意义上的戒德。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来自于前述的戒德内外两层次的相互契合。由于内外领域相互关联,使得其中一方可成为工具,给另一方造成深刻持久的变化。正如心态以身或语的作为对外表达自己,同样地,某种行为的止持与作持能够反过来作用于心,改变心灵生活的基本倾向。如果说,为贪与嗔所主宰的心态可以导致杀生、偷盗、说谎等行为,那么对杀生、偷盗、说谎的戒离,亦可以产生仁慈、知足、诚实、真语等心理倾向。因此,道德纯净意义上的戒德,也许不是灵性修练的起点,但恪守端正的操行原则可使之最终成就。
连接sila的这两个维度、并协调外在行为向内在纯净转译的媒介,乃是动机或者说意志(cetana)。动机是每一个体验俱有的心理因素,与每一个意识活动普遍共存。正是这个因素使体验有其目的性(teleological),即指向某个目标,因为它的具体功能是引导它的相关诸要素达成某个特定的目的。佛陀教导说,一切业 (kamma) ,本质上即为动机。因为动作本身,终究是动机透过身、语、意三种行动之门的体现:“比丘们,我说动机即为业。因为动机既发,他借着身、语、意造业。”
动机决定着业的种类,由此给业赋予道德意义。不过,既然动机存在于每个意识状态,它本身并无伦理特征。动机从某些称为根(mula)的别种心理因素得其特定的伦理品质,在主动的体验情形下它总是与根共同升起。根在道德定性上有两种: 非善巧(akusala)与善巧(kusala)。非善巧根为贪、嗔、痴,善巧根为非贪、非嗔、非痴。后几种虽然以负面形式表达,其意非仅是染垢素质之无,还指相应的正面道德素质之有——它们分别是: 施予、慈爱、智慧。
当动机由贪、嗔、痴的非善巧根驱动时,它以恶行的形式——杀生、偷盗、私通、谎言、谗言、谩骂、闲谈——突破身语之门而出。以这种方式,心理杂染的内在世界使时空延展的外在世界阴暗化。然而,动机的污染倾向虽强大,并非不可逆转。非善巧的动机可以被善巧动机取代,使精神生活的整体倾向接受根本性的逆转。动机的这种逆转,其发端乃是自愿持守属于一种正态秩序的操行原则——即愿意戒恶修善。接下来,当有暴发为恶行倾向的动机被约束,代之以相反的动机,代之以言行有德的意志时,一个逆转过程即已开始,坚持下去,可以使品性的道德基调发生深远的转变。这是因为动机的诸种作用,非是把全力施行于当下活动,而且还对生起它们的心流起着反推作用,引导那道心流转向它们本身的趣向: 非善巧的动机引向恶趣,善巧的动机引向善趣。于是,每一次一个非善巧的动机被其相反的善巧动机所替代,从善的意志即被强化。
素质的替代过程,以不相容的心理素质不可能共存于同一个体验刹那的法则为构造的基础,接下来,借着相关之根的效力达成转化。正如非善巧动机的升起必然带着非善巧根——贪、嗔、痴——同样地,善巧动机也必然带着非贪、非嗔、非痴的善巧根。既然对立素质不可能同时存在,善巧动机对非善巧动机的替代意味着善巧根与非善巧根的置换。善巧根性被涌现的动机不断地唤起,便以其素质——施予、慈爱、智慧——“熏染”着心流; 这些素质随其力量的聚集而凸显为个性的惯常习性。以此方式,善巧动机在种种场合下的重复,使得个性从原先道德上的易腐性,转变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纯净,甚至对邪恶的诱惑亦能够安然远拒。
虽然动机或cetana是转变的主要工具,该意志本身却是无定性的,必须有具体的指南把它的能量引向善的实现。从佛教观点来看,单有“善意”是远不充分的,因为动机虽然高尚,只要持者的智力为痴迷的尘垢所遮蔽,可嘉的愿望总是有可能以愚昧甚至毁灭性的行动轨迹表达出来。这种例子在过去已有太多,至今仍然令伦理泛论者[1]常年头痛。根据佛教的观点,意志的良善必须转译成具体的行动轨迹[的良善]。它必须受端正操行之具体原则的统辖,这些原则在应用上虽然灵活,却有其值得作为遵守原则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独立于任何历史上的文明与现存的价值系统,完全是因为它们符合道德报应的普遍法则[=业力法则],以及它们在修行道上的重要性,这条无时相之道引导我们从苦与轮回世界中解脱。
为了引导意志追求善德,佛陀以明确的语言给出了道德修练的要素,我们必须完善它们,才能够确保在觉悟道上获得进步。这些要素构成了八圣道中的三项戒德蕴: 正言、正业、正命。正言指避免一切伤害性的言语——戒谎言、谗言、谩骂与闲谈; 行者的言谈必须永远真实、利于和谐、温和、有意义。正业要求停止非善巧身行,即戒离偷盗、不当性事(这对比丘来说意味着非独身,对居士意味着通奸及其它被禁止的关系); 行者必须常具同情、诚实、纯洁。正命要求避免对其它有情造成伤害与痛苦的职业,如贩卖肉类、奴隶、武器、毒药与醉品; 圣弟子戒离这些有害的生计,以和平正当的职业活命。
八圣道当中上述几支所蕴含的训练要素,同时既抑制着人类心智中低等、非圣、毁灭性的冲动,也促进着一切超凡、纯净的行动。尽管以负面词性表达这些规则意欲排除的种种行为,在效果上却是正面的,因为当它们被纳为行动指南时,激发健康心态的生长,后者终究体现为良善的行动轨迹。在深度上,这些戒律直趋内心隐僻处,挫败非善巧动机的力量,把意志转引向善德的成就。在广度上,它们延至人的动荡的社会生存,遏制着竞争、剥削、攫取、暴力、战争的潮水。在心理维度上,它们赋予心灵健康; 在社会维度上,它们促进和平; 在灵性维度上,它们是成就解脱道一切高等进阶的无可替代的基础。常规地受持与修习之下,它们制止一切以贪、嗔、痴为根性的心态,促进以非贪、非嗔、非痴为根性的行为,引导人们度过施予、慈爱、智慧的一生。
可见从佛教角度看,操行的具体规则,并非是良好意愿之外的多余附件,而是对正确行动[正业]的必要指南。它们是修练的基本成分,当这些规则被意志力付诸实施时,即成为净化的根本手段。特别在禅定修持的背景下,戒律防止那些毁坏禅修目标的垢染业的发作。审慎服从操行的既定规则,我们可以安保自己至少戒离了贪、嗔、痴的粗相表达,我们将无须面对逾越常规道德所招致的自责、焦虑、不安等障碍。
如果我们回到前文中对佛教修持的大树比喻,把戒德作为根柢,操行原则即是根柢的生长土壤。正如土壤包含着助树苗抽芽生长的养分,戒律也包含着灵性生活需要的清净与德性的滋养。戒律所表达的,乃是阿罗汉的自发操行。对阿罗汉来说,操行是他的内在清净的自然流露。他的一切行为依其本性无瑕无染。他的行动不可能以贪、嗔、痴、惧为动机——非是因为他被迫服从规矩,而是借着他的存在法则。
不过,凡夫对不道德行为是不能够免疫的。相反,由于非善巧根性继续固植于心的内在结构,他时时朝着逾越道德的方向倾斜。他有可能杀生、偷盗、私通、说谎、饮酒等等; 没有对这等行为的明确禁戒,他将时常屈服于此种倾向。因此,有必要为他提供一套建立在智慧与慈悲基础上的伦理准则,藉此调御自己的行为,使之与解脱者的自然、自发行为和谐一致。
因此,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戒律远非是强加于行为的无端禁制。每一条戒律具体表达的,是一种相应的心灵态度与精神原则,该原则以切实的行动模式,包裹着内在的一道清净之光。戒律使不可见的清净态成为可见; 透过身与语的媒介,折射为诸项具体的操守规则,为我们所把握。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些规则所覆盖的种种情形之下时,把它们作为行动指南。我们使操行与戒律和谐一致,藉此滋养我们修行的根柢——戒德。当戒德被牢固确立起来时,圣道的后继阶段将依照修道的法则自然展开,在达到顶峰之际,成就圆满的智识与解脱的宁静。如世尊所说:
比丘们,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无悔。”比丘们,对拥有戒德、具足戒德者,无悔为法[自然法则]。
无悔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愉悦。”比丘们,对无悔者,愉悦为法。
愉悦者,无须作此思:“愿我生喜。”比丘们,对愉悦者,喜为法。
喜者,无须作此思:“愿我身轻安。”比丘们,对喜者,身轻安为法。
身轻安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乐。”比丘们,对身轻安者,乐为法。
乐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定。”比丘们,对乐者,定为法。
入定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如实知见。”比丘们,对入定者,如实知见为法。
如实知见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厌离。”比丘们,对如实知见者,厌离为法。
厌离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离欲。”比丘们,对厌离者,离欲为法。
离欲者,无须作此思:“愿我得解脱知见。”比丘们,对离欲者,解脱知见为法。
如此,一阶流向续阶,一阶引生续阶之具足,为从此岸到达彼岸。(增支部 10:2)
(本文来自原作者同名文集。)
中译注
[1]: 伦理泛论者(ethical generalist)的定义,据尊者对中译者的解释,是指“那些认为我们只要坚定承诺行事有道德感即已足够,反对把该道德态度明确表达为具体操守规则者。”
相关热词搜索:
分享到:
 收藏
收藏
评论排行
- ·死到生——业在死亡和投生过程中的作用(0)
- ·初果圣人只剩七次人天往返。如果这七世...(0)
- ·原始佛教与现存的上座部佛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