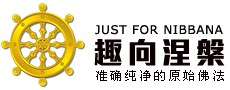年少修行忆事
我在台湾出生,出生的时候,佛陀已经入灭了近二千五百年。小时候,我有时会带着一种惶恐的心情靠近镜子,望着镜中人,摸摸脸,揑揑身体,问自己:「这是谁?」我甚至于闭起眼睛,注意呼吸几分钟,努力的想自己「生从何来」,然而答案依然没有浮现,我总有懊恼的感觉。那时,我觉得大部份的人,每天活着,活得那么的老神在在,竟然都不会想要出离一再循环的生死牢狱(rodha, Vism.495),实在不可思议。隐隐约约之中,我似乎已在寻根,寻找一条能够「终结生死」(ni-rodha﹐灭,无牢狱(之灾) )的理路。
在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就由父亲的口中得知,印度曾经有一位释迦牟尼佛,因为体悟了人生有生、老、病、死的苦,于是透过修行而悟道(脱离生死轮回)。佛陀的修行故事,在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可说是记忆犹新,这让我更加的肯定──确实是有个「出脱生死之道」;那时,我生起了想要修行的心意,可是又不敢说出来。家人及身边的人都没有在修行,我没有可学习的对象,也不知道何处可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缺乏老师及经书的引导下,我也只能独自摸索。
一、观四大、不净
1962年,在我国小五年级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一节「劳作课」,是要将一块一块胶制的人体五藏六腑,贴在硬纸版上的正确位置,当我看到人体的各种内脏时,有种恶心感。之前我也看过人体解剖图,但总是有回避的心理,所以没有看仔细;而那次,我特别定睛看大约五公分四方大的小肠子图像。虽然肠子跟其它脏腑都制作得很粗糙、不逼真,但是我看了之后,鼻头略有痒痒的感觉,再仔细的看和感觉,似乎有一个口罩罩住我的口鼻。当时,我想着肠子是软软的,于是就取软软的感觉;吸气与呼气,则取不净物中的软相。虽然,那时的心思不能说是达到念念分明,但是整天都是与软相为伍。
学期考试结束,放暑假了,我还是一直取软相,结果脸部似乎有点扭曲变形,身体也软趴趴的。这是自己找的,不知道是不是自找麻烦;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身体出状况,大概医生也救不了。但因为自己还做得了主,所以敢持续地观软相,不过也不敢全然投入,因为全神贯注时,就会马上加重脸部的扭曲变形及身体的柔弱无力。大约观了半个月左右,感觉似乎没有结果,所以就放弃,不再作意软相了;再经一周左右,我才恢复正常,前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敢照镜子。
取「软相」兼「不净观」作为禅修的对象──是我四十一年前初次修行的小插曲,不很正点。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有所谓的「不净观」这种修法。现在,我还是会怀疑,在那个年代台湾有人会修「四大差别观」,或曾实修过「不净观」?以修「四大」来说,实际的修法是四大的十二个特相,反复的修软、硬,冷、热…等,直到证得近行定(靠近初禅的定),而可见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并继续修行色法(物质)的透视等等禅法。至于修「不净观」,则取不净相,并辅助以默念该不净相样貌的名字(如:厌恶的脓烂、厌恶的脓烂…),直到得初禅(安止定﹐完全地全神贯注)(详见:《清净道论》第十一品、第六品﹐Vism. 347f.、178f.)。
当我开始摸索修行时,未满十一岁,但我却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因为迟修了几年,少说也有五、六年。再者,以轮回来说,我已经是宇宙老人了,已经错过无数次修行得解脱的机会。以修行来说,实际上,大约六、七岁就可以修行证阿罗汉果,七岁以前不现观涅盘,是因为「心无力、细小、迟钝、不清晰」(见《弥兰王问经》下卷〈第八品〉第八)。而我迟修了,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修得对不对。
二、呼吸法
1963年,在我国小毕业后与上初中之前的那个空档期间,我曾经用七天的时间来练习观呼吸。当时的我,对「戒定慧」、「四圣谛」及「八正道」一概不知,只知道静坐时要注意呼吸,于是取「呼吸」作为禅修的对象,日夜注意呼吸,让心能念兹在兹。那段时间,除非有必要,不然不说话,说话只是应付一下,很简短,我不敢完全禁语,怕被家人知道,会故意吵我,我就破功了。好佳哉(好在),家人并不知道我在秘密地进行「观呼吸」。
当时我对「呼吸观」、「数息法」、「入出息念」等,这些名词一无所知,细节则更是无知。我只会注意呼吸,但不懂得「数」呼吸,不过心还是能专注在「呼」、「吸」上,跑掉的机会不多,我可以守住呼吸一直到入睡,一醒来也能马上守住呼吸,那时几乎是全天候的「念住」。至于坐姿,静静地持续坐着的时间并不长(最长也只有二十分钟左右),因为坐久身体会不舒服,也不知道如何克服;而且,那时家里的空间是整个开放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看到,所以在静坐时,有时我还得动手动脚,装模作样,好让家人不会觉得我有异样(在静坐)。我常常变换姿势,静坐、动作、来回走动,就是一直守住呼吸。这次没有修不净观时的后遗症,所以可以更专心的修习了。
大约在第六或第七天下午的时候,我骑脚踏车到新学校去看环境。黄昏时,在骑车回家还剩一百公尺左右,我心想着:我守住呼吸那么久了,怎么没有什么结果?那时,我没有懊恼,没有期待。想想,会不会专注还不够?在多踏几下踏板,让车子滑行之后,就只是加强观察呼吸。不到两下,在呼气的时候,看到亮光及心念快速生灭,仅维持几秒钟;而当心念慢下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觉知一秒钟有数十、数百下的生灭(实际上,一秒钟有数亿次生灭)。当时,我还骑在车上,没有闭眼,没有跌倒,心念快速生灭,心脏也蹦蹦跳。还有,身体有点麻木,手脚活动不太灵光(见到无常者,不一定有此现象),我有点吓到。
此刻,我了解到,原来心念是一念灭了,新的一念紧接着快速生起,一秒钟有无数个生灭;我也了解到,造因(造业)亦是一念一念地累积。虽然,那时我对因果的观念,还是无法以追溯前因后果的方式来全盘贯通,但是追溯根源的倾向,已若隐若现的在我心中萌生。
心念快速生灭,前后才持续几秒钟。我的心念变得很清晰,一举一动了了分明;有一段短时间,记忆也变得超强,但是没有测试是否可以过目不忘。我守住呼吸六、七天,事先并不知会发生什么状况,当然也不知道会见到「无常」,我只是有一股傻劲,认为自己再不修行不行的迫切感。观察到「无常」是美事一桩,也是愉快的经验,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在修道上的意义与作用;不过,我知道修行里面还有很多的秘密,正等着我去探索。
能见到「生灭法」(udayabbayam)是非常难得的、佛陀所赞叹的,《法句经》113偈说:「若人寿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得见生灭法」。「一日」(Ekaham)在此可作「一时」解释(参考《法句经故事集》) 。观察五蕴(物质与精神)的生灭,再更进一步的话,可进趣涅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可是中国的高僧传中,竟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高僧见到「生灭」或「无常」,不知道是私秘起来,或者已经被「生灭即无生灭」、「常无常不可得」的玄思搅乱了,而以为「无常」是小儿科(微不足道)或小乘法。
三、四念处
少年时期,我读了一些禅宗的书,似懂非懂,对正法的知识增长不多。
1973年,我上了大学,参加佛学社,看到了市面上看不到的佛书,于是就开始拼命读。那时,我对修行很投入,有道业比课业重要的取向,「大事未了,如丧考妣ㄅㄧˇ」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
我也去听学社开的「十四讲表」,虽然我对「净土」的观念不以为然,但是当我听到「无常」的道理时,感触很深,才开始正襟危坐的听法。为了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念佛法门及「念佛三昧」,1974年年初,我去参加一次佛七。「念佛」毕竟是比较感性,在第三天,早斋结斋时,梵唱回向偈,我的心被触动了。之后,连续几天一出声念佛,眼泪就夺眶而出,不能自主,这是我一生中流泪最多的经验。那时,我对「佛」有「如子忆母」的感觉,似乎已睽违佛陀良久。
1974年四月,学校的春假有七天,我留在学校宿舍度过。宿舍只剩我一人,佛学社的社友也都走了,校园冷冷清清的,除了睡觉以外,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待在佛学社禅修。那时我修习正念的知识还很浅薄,主要是来自《佛陀的启示》第七章「修习:心智的培育」及《原始佛典选译》中的〈大念住(经)〉。那几天,我安排打坐、经行,不看书,不讲话,只观住呼吸;动作、走路时,则兼顾观察「连续」动作、「连续」走路。「连续」的意思是:慢慢做动作,但是也没有特别慢,「慢」只是为了更细腻的念念分明,并兼观动作的生灭。这样的反复练习是生灭观的遍作定(parikammam预备)。虽然,经书上并没有提到,需要这样做来增加正念;但我那时却觉得有这个需要。后来我才知道《清净道论》(Vism. 104、621)有提到,而且有些南传的禅师也这样指导。
关于呼吸的方式,我常常观察呼吸触击鼻端 (parimukkha﹐人中及其附近)的触觉生灭:
呼→触生 呼→触生 呼→触生…
吸→触生 吸→触生 吸→触生…
我保持觉知「触觉」的「生」(呈现)与「灭」(消失)。「生」:就是在呼或吸触击鼻端时的触觉;「灭」:是当呼或吸停顿一下时,没有「触觉」时的觉知之称呼。新触觉的生起(现见法),就是前一个触觉已灭,后一个触觉尚未生。「触觉」的生(呈现).灭(消失)、生.灭、生.灭…的轮番交替,是我用来现观生灭或无常的方式。当然,每一口气不一定要顿三次,可以顿更多次或只顿一次。「顿」是:极短暂的停顿,即使极轻微也可以。在正常呼吸的节奏中,略略觉知呼或吸的停顿,不一定要出声。实修时,原则上呼与吸都可以顿,但是这样做会比较累;可只选其中的一个,我大部份都集中在呼气时顿,或加强观照。当然,不管什么时候,若感觉累,就恢复自然的呼吸,保持觉知呼吸的触觉就可以了。呼、呼…,吸、吸…的造作,属于呼吸四相「风、喘、气、息」的「喘相」(不管有声或无声﹐但不是急促)。天台大师说:坐时鼻中息出入觉有声是「风相」。坐时息虽无声而出入结滞不通是「喘相」。坐时息虽无声亦不结滞而出入不细是「气相」。不声、不结、不麤,出入绵绵,若存若亡,资神安隐,情抱悦豫是「息相」。(大正藏46.466上) 。依修定来说,风相、喘相、气相被判定为不调相,心难平定。然而,在我的经验里,修直观无常者不但不用忌讳,而且应常常加以应用,甚至每次静坐都可以使用。若呼吸已调到平顺的「息相」,因为「心一境性」的特相逐渐显著或已稳定,需作意转移至觉知呼吸的「触觉的生灭」,这样做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品尝到更微细的无常。
我使用风相、喘相、气相来做无常的观察,其中以「喘相」观测「触觉的生灭」(无常),对我来说,是最直接的(现前的、非想象的)、最真实的(可触的、可觉知的)、现见法的(当下马上可见到的)。观察呼吸的触之生灭,与缅甸韦布西亚多(Webu Sayadaw 1896-1977﹐传说他是阿罗汉)的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修法。(他的教法,请见〈智能的语言〉、〈见法之道〉《嘉义新雨杂志》第17期﹐1997.1.;Selected Discourses of Webu Sayadaw﹐Translated by Roger Bischoff﹐ 1992.)这个方法可以在未完成八种定、十种遍禅或一阶一阶的细修观禅(vipassana毘钵舍那、内观)之前,即能直接观到无常,乃至体证涅盘的快捷方式,而三藏经典中并没有明文记载由此法(觉知触觉的生灭)趣入,这是千年不传的秘藏。就我所知,韦布并没有指导「喘相」,但是私下的教学,我就不得而知了。1998年,当我到「上缅甸」瓦城之南Kyause(叫些镇)的Webu Monastery(韦布寺)拜山头时,倍感亲切。
我还有一个辅助修行的方法,也是自己的独门工夫,但是比较难表达,就是:在呼吸时,特别是在呼、呼…时,心中加猛力(勉强可说是精进力及培育瞬间的定力),作意要入「甚深法界」,去破无明壳。我的灵感来自「无明壳」这个佛学名词,我想,无明的「壳」是很硬或者是很顽强,众生才被困其中,所以就用这种作意的方式。《清净道论》〈第八品〉说〈安般念〉时,有提到呼吸十六事(十六特胜)中的第16事,有「遍舍舍遣」(pariccaga-patinissaggo完全舍弃之舍离),及「跳入舍遣」(pakkhandana-patinissaggo) (Vism.290)。但是,我的加猛力的作势,跟两种「舍遣」(舍离)并非完全相同。论文是说:完全舍弃(蕴及诸行的烦恼)→跳入涅盘。而我的作意方式是:加猛力作意要进入法界深处,破「壳」而出(无明壳破了﹐等于完全舍弃世间烦恼)→跳入涅盘。在《律藏》〈经分别〉「波罗夷」,佛陀说:「于此世唯一破‘无明(蛋)壳’(巴avijjanda-kosa﹐梵avidyanda-kowa),证无上正等正觉者。」用「壳」来作比喻无明的状态;而我的作意方式就是取这个「壳」来当作突破的假想对象。
加猛力破「壳」虽然比较抽象,但是经过实际操练之后,应该会是一个有力的助缘;不过这个作法,尚未被公开检视过。有些禅修者,特别是「纯观行者」(sukkha-vipassako﹐未得禅定的纯粹观行者),虽然能观察到生灭,但仍无法更进一步的突破,不知他们是否正缺少了这个猛力「向上一着」的「波罗蜜」(parami﹐最超越的)? 禅修前三、四天,我每天还几次刻意想象「(五)欲境」(色、声、香、味、触中的某一项事情),然后甩掉;作意「(好、坏)情境」、甩掉,作意「色相(或女人)」、甩掉;…;现前的情境也是被我作意甩掉。如何甩?就像用一只无形的手,捉住情境,再甩掉。如此持续反复的练习,是可以伏断相续不断的欲望及更深层的潜在欲念。我就是用这个方法,作为禅修的辅助资粮,一天用三.五分钟,将世间的欲望一一舍弃。这是我「诃(责)五欲」(借用天台大师之语) 的方式,没有人教我这样操作,结果我镇伏了五欲,六根触境变成无好恶(upekkha﹐舍),更贴切的形容是「枵(ㄒㄧㄠ,空朽)木死灰」的特别觉受。到达这个境界,保持在这个境界时,我就不再这样作意了。经中所说的「一切世间不可乐想」(sabbaloke-anabhirati-sañña)的顶尖成就,应是六根触境变成无好恶的状态。经文对此并无任何解释,只空留名词,是很难让人去实践的。
中国行者偶而有人会达到守护六根成为根境接触无好恶的状态,而且自然运作(anabhoga﹐无功用行,不加造作的用功),但是无以名之,也不被肯定。禅宗公案有「婆子烧庵」的故事引为鉴戒(负面的教材),禅宗行者否定修成「枯木」、「寒岩」的状态(「(我好像)枯木(一样地)倚(靠在女子身体,像)寒岩(一般没有感觉),(即使)三冬(=年)(,也)无暖气(=不生欲望)」);但是,那种境界若能成为往后修行的增上缘,又有何不可呢?
禅修四、五天之后,我省察内心,感觉似乎有些微的急切或者说紧绷,但是这个状态是不太容易觉察与下判断来确认。我想到佛说的弹琴譬喻(《增支部》A.6.55.;《杂阿含254经》;《增壹阿含23.3经》;《中阿含123经》…等),琴线不可太紧,亦不可太松。于是我想,试着稍做放松也无妨。我放松一些些,放松中又能精进、不涣散,慢慢的去拿捏。当时,打坐时的念头还很多,每一分钟内还出现好几个,有点沮丧;后来就随它去,只守住「念」。那时我并不知道,对「纯观」行者而言,只要守住「触」这一个主要目标即可,其它的次要目标,如念头多、身体痛…出现时,不用去在意它或觉得懊恼,就让它自然的生灭,不一定要「打得念头死」。
另外,在禅修第四、五天,内心主动生起对过去所作的过失生起悔意,我至诚恳切的表示忏悔。在当生中,曾诽谤佛陀、圣者、佛法,就会障碍证圣果或更进一步的果证(Vism.425)。只要说的话,不是佛陀(或圣者)的话,却说成佛陀说(或圣者说)的,不是法(=非法),说是法,就是构成诬谤。当时我还不知道诬谤三宝的严重性,以及忏罪的必要性。
在第六天下午黄昏时(我黄昏打坐,心较容易平定;每个人都有差异),我闭眼打坐的时候,心想,五蕴中没有我,一蕴一蕴的想过,花不到一分钟的省思,然后再注意呼吸,不到两个呼吸,忽然眼前慢慢大亮起来,前两天也有两次亮光闪过。这次眼前亮起来,可以用比太阳光还亮来形容,而且还持续亮着。不仅如此,我见到心念快速生灭,越来越快,像一直掉入万丈深渊,我虽然有点恐惧,但是还是顺其自然,以「准办死」的心理去迎接它。心念快速生灭当中,还进入更细的生灭,其中又分几个阶段。当心念快速生灭停下来之际,进入一种「宁静」(santa),极短暂地停留,心脏又跳动一下,然后离开「宁静」。心念生灭的整个过程,前后不到十秒钟。
心念快速生灭的最后阶段,我感觉头顶百会穴附近的头壳有裂开三次的感觉,心脏也有「暴动」的感觉(据《人施设论》中说,等首阿罗汉(samasusi)证得阿罗汉之后,即刻死亡,可能是心脏麻痹的缘故。)。所以当这些情景停下来之后,我第一个动作是摸摸头壳有没有破裂,还好,没怎样,再摸摸心脏,也没怎样,我就放心了。再感觉那种「宁静」,很奇特,一切存在(的欲望)完全灭绝,已经无法用六根触境无好恶来形容。我无喜、无乐的感受,我原以为是时间极短(比一秒还少很多)的关系,其实那「宁静」是无想(没有办法「想」)──难怪我误以为是晕眩,当然也没有办法觉知感受;当离开那「宁静」时(因为已离开情境),同样是感受不出,即使「宁静」中有喜、乐的心所(cetasika心的因子、心的伴随物),持续七天七夜,同样是感受不到。此中喜、乐及其它的心所,必须有「名色分别智」(nama rupa pariccheda bana),才有能力省察已发生过的心与心所。那种「宁静」绝对不是完全专注的禅定,因为当时的心是如护油钵(不令油溢出)的一直锁定「生」、「灭」;那也不是短暂昏沈一下,而掉入有分心(Bhavavga﹐六根不接触六境的无记心状态),在生死交关的时刻,怎么可能打盹?
过后,我没有任何激情,内心有一种未曾有过的「宁静」,说「死寂」更贴切。我有生出「眼」的感觉,以前是有「眼」,但是是瞎着,前后对比,判然有别。我发自内心的深处,归依佛、归依法、归依贤圣僧。「归依、信仰佛陀及贤圣僧」的心意是:肯定他们都是毫无疑问的解脱者,这是将心比心;「归依法」的心意是:不会想要再寻找或构思比佛法「更殊胜」的法,相信这样依法修行,必定能究竟解脱。之后,在白天,我的眼睛每次闭眼,张眼之际,似乎有两道光线,从眼睛中射出,维持两年左右。
「宁静」的后续力很强,我有种「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心境,我已知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生灭法、充满苦、无价值的,甚至说世间的存在是荒谬的;换句话说,「生命无意义」(缅甸帕奥禅师(Pha-Auk Sayadaw)也这么说过)。那时肉体的知觉消失很多,摸起来不太有感觉,而且持续多日。我有视死如归的心态,感觉活片刻,就是累赘,但是没有想要马上去死的念头。佛陀说「所有受皆悉是苦」(‘Yam kibci vedayitam, tam dukkhasmin’ti. S.36.11 / IV. p.216),佛陀是依诸行无常而说的,修观禅者确实可见到微细之「苦」(三法印之一),但我在离开观禅之后,比对「宁静界」(非观禅)与生存界,我完全明白生存本身就是苦,这并不是沉浸观禅者所能理解的。我的心情很像舍利弗尊者所说的:「我不乐死,我(也)不庆生。」(“Nabhinandami maranam, nabhinandami jivitam.”)(《长老偈》Theragatha v.1002)。
我能完全理解经典故事所说的,闻佛说法得初果或更高果位的圣者,不用多加考虑,马上可以舍弃一切,跟佛陀出家。因为亲证者已经有「法眼」,而且一较量「世间」与「出世间」(涅盘),立即可舍弃无价值、无意义的世间,这絶不是用概念思索出来的。世间与涅盘明明有差别,后代的论师还是要创造世间与涅盘「无毫厘差别」的惊世之语。
禅修结束后,接下来的十天左右,没有烦恼生起。只感觉心念很清晰,先有念头,再有动作;念头一个,动作一个,两者分开。头两三天,连呼、呼…,吸、吸…,都还会感觉身心分离。念头生灭、生灭,念头、说话、动作如果太快,感觉会乱掉身心「一生一灭」的步调,所以我念头、说话、动作都放慢,有时像在做慢动作。名色(身心)分离的现象,往往会发生在禅修者身上,特别是修持毘钵舍那的行者,近代缅甸马哈希西亚多(Mahasi Sayadaw)在1950年代开始弘扬毘钵舍那法门以来,在缅甸已广为人知,只是我当时一无所悉。
「烦恼是否会再生起?」是我重要的检测指标。大约在禅修结束后十天左右,生起一个微细的烦恼(瞋念),我才知道烦恼还在。在观力消退之后,正念弱时,贪、瞋、痴就轮番上阵了。
四、结语
回顾自己年少时的修行过程,由于能取得的知识有限,因此,在修行道上一路走来,总是披沙沥金,方得法宝。而现在,文中所夹带的经证及论证都不是我当时的知识。那时,我何尝不愿意依止 (大)师(sattha﹐garu)或明确的道迹(patipada)来走,但是生在罕有正法的边地,先天上就难遇到正法,明师更是稀罕,所以,自己只好坚强起来当独行客。
我的实修经验三、四十年未曾公开,而近来我如此思惟:是否应该为禅修者留下一些可资参考的道迹?经过考虑后,我决定以报「事」不报「名」(隐名)的方式来陈述。于是,我就慢慢的回忆,清理陈仓旧货,用「偷渡」的方式来发表。然而,像这样的述说,有时我还是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甘寂寞而堕落了。
我对存在的生命的焦虑感及无归宿感已消失,我自忖报佛恩,愿意当佛门义工,推动佛法一阵子,一方面也继续学习正法。但是岁月如梭,匆匆又经过三十年,我已经是发白齿摇了,生死还未了。虽然,当我正念相续时,还是可以见到无常,但是威力不强,这跟我近年来密集禅修不多,及修「止禅」(samatha﹐集中专注的禅法)的取向有关。不过,我还是很有自信,在短期的密集「观禅」中,还是可以再进入更深的「无常观」,毕竟这条路自己亲自走过,已有道迹可寻。
佛陀说,人生三个时期,应该要有一个时期来修行(《法句经》157偈)。我已经错过少年期、中年期,不应该再蹉跎岁月了!
愿 一切有情﹐循法觅道﹐出生死牢狱 。
(编按:本文未署名,列为无名氏。)
(2005.5.15.订正) (原载《法雨杂志》第2期)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心灵天堂之旅――内观十日心得
下一篇:谛观入门必读(2008年校译版)
评论排行
- ·死到生——业在死亡和投生过程中的作用(0)
- ·初果圣人只剩七次人天往返。如果这七世...(0)
- ·原始佛教与现存的上座部佛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