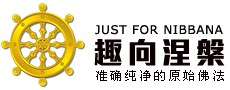S. N. Goenka
(故事形式的自传)
尼泊尔Shri Yadu Kumar Siddhi先生曾参加在菩提迦耶(Bodhi Gaya)举办的内观课程,受益良多,他的许多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很快地,他们开始热切地要求我在尼泊尔Birganj或加德满督指导课程。
为了指导法和其它理由,我也想拜访尼泊尔。对于喜马拉雅山生气盎然的有益共鸣,我感到了莫大的吸引,也觉得适合禅修,但那儿还有一个更大的吸引──尼泊尔诞生了昊天网极的伟大生命:佛陀,是他重新发现了内观这个方法,并为众生开启一条解脱之道。
但那时我无法造访尼泊尔,因为我是缅甸公民,缅甸政府非常好的给了我护照,但只能在印度旅游。
为了尼泊尔人的利益,1972年九月我在印度的Raxaul指导课程,它位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参加的人有一些是来自边界另一边的Birganj市,也有一些是来自加德满都。此外,许多从Birganj市来的非禅修者也允许他们听课,但只限晚上开示。
课程顺利结束后,Birganj市的人们强烈要求我在他们的城市指导课程,主要是Birganj的设备要比Raxaul好,且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课程。我跟他们讲了我的难处。他们响应:「先生,你有印度血统,只要穿dhoti kurta(印度传统服装,dhoti是长缠腰布,缠于臀部和大腿,kurta是白色无领宽松上衣)就可轻易地通过移民局穿越边境,印度与尼泊尔的人民不需签证就可自由出入彼此的国家。
但这个建议完全不被我接受,因为在这之前,我的老师乌巴庆已为我树立高贵典范。乌巴庆老师极想到印度,借着将这个美妙的内观方法传回它的发源地,来亲自报答他的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方法在印度已经失传。所以他向当时的缅甸政府申请护照,但碍于政府的政策,除非他永远的离开这个国家或受海外聘雇,否则不可能拿到护照。
我对于当时缅甸政府的内阁秘书U Win Pe来国际禅修中心看乌巴庆老师的记忆犹新,他是被内政部长Col. Kyaw Soe派来告诉乌巴庆老师这件事;其实不只内政部长,所有内阁的部长都非常尊敬乌巴庆老师,但对这件事他们也都很无助。所以,U Win Pe建议乌巴庆老师从他一位海外的学生取得聘用书,但这个建议并非基于事实,因此完全不被乌巴庆老师接受。
怎么可能教导纯净的法,但跨出的第一步却违反戒律?法的传播如何能真正成功呢?我将这个教导法的基本原则牢记在心,因此也没办法接受Birganj人们的提议。我非常坦白的告诉他们我是缅甸公民,所以不能跟尼泊尔的移民局说我是印度人。
一个非常富有的尼泊尔企业家也参与了这个课程,他在尼泊尔许多不同的政府部门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建议我坐他的车进入他的国家,移民局的官员甚至也不会问我是不是印度人,用这种方式,就可避掉说谎,但我怎能接受这种建议?毕竟,假的就是假的,欺骗就是欺骗。因此我没办法去尼泊尔,只能继续在印度上课。
光阴流逝,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来印度参加内观课程,他们开始请求我到他们国家指导内观课程。他们说,这样他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其它数以千计的人即使无法前来印度,但也可经由这个美妙方法受益。他们深信西方人士将会欣然接受这个科学的、理性的、非宗教派别及具有成果导向的内观方法。
相当准确,我可敬的老师也相信内观这个纯净的方法将从印度传遍全世界,但除非能在别的国家指导课程,否则法怎么传出去?因此我向新德里的缅甸大使馆申请,请他们在我护照上核签到其它国家。
大使馆的大使和其它官员都很熟悉我,对于我从事法的工作也很高兴,亦极渴望帮我将内观带到其它国家,但给予新的核签并非他们的权利范围,所以将我的申请转给位在缅甸仰光的外交部,而碍于当时缅甸政府的严格政策,我的申请被驳回了。
于是我呈递一份申诉,详细说明为何这件事至关紧要,因为它关系了全世界很多痛苦人们的利益,所以我必须亲自到各个国家去指导他们内观。但大使馆拒绝转递我的申诉,因为他们确定位于仰光的政府当局不会接受,因此,我只能继续在印度开课。
更久之后,国外学生的催促增加,于是我写信给在仰光的朋友U Thi Han,他获悉有这么多西方国家对法有需求,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我应该去那儿指导课程。
当初也是因为U Thi Han持续努力,才得以让我拿到护照回印度为我母亲服务,那时我母亲正遭受心理疾病之苦。U Thi Han当时是缅甸的外交部长,但现在退休了,那时他要我寄一份申诉给那时的首相Col. Maung Maung Kha,他负责将我的案例呈给首相。
Col. Maung Maung Kha 是我很好的朋友,临时政府期间,在U Thi Han的领导之下,我两次参加政府的贸易代表团到印度、苏联和欧洲的其它共产国家,Col. Maung Maung Kha曾是这两个代表团的成员,他之前就认识我了,但在国外拜访的期间我们更熟。
改革政府掌权后,他被任命为工业部长的秘书,稍后则成为工业部长,然后晋升成为首相。因为和Col. Maung Maung Kha这层亲密关系,我希望他会接受我的申诉,除了申诉书外,还写了一封个人信件给他,然而并未收到他的答复。
虽然他对于传播法这件事非常高兴,也引以为傲,但似乎也没办法改变那时严格政府的政策,他也无可奈何。
几年之后,1990年在缅甸政府的邀请下,重游缅甸祖国,那时U Maung Maung Kha已经从首相退休。很多我的老朋友来见我,并且恭喜我的成功,我记得U Maung Maung Kha是第一个来到我儿子U Shwe's住所见我的人,他极为高兴且恭喜我在法的工作上的成功,然而当他还是首相时,因碍于当时严格政府的政策,而无法接受我的申诉,核签我到海外传法。所以除了印度外,其它国家我都不能去。此外,尼泊尔的学生又再次提出他们之前的论辩──印度人不需护照就可以进出尼泊尔。有一次课程,一位尼泊尔的高层官员也参加了,同时他保证可以安排我造访尼泊尔,且可负责我在尼泊尔的全部行程,但是,显然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我深觉做为一个缅甸的公民,除非缅甸政府允许我,否则印度以外的国家我都不该去,即使这个理由是多么地冠冕堂皇或是这个行程是多么安全无虞。
这不单只是政治和法律障碍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责任。如果我是到尼泊尔去授予纯净的法,那我就不能在错误的基础、违法的抉择来教导。因此,再一次我拒绝接受尼泊尔学生们的请求去拜访他们。
今天,当我回顾这所有的过去,在法上我感到极大的满意:我那时的抉择真是正确。假如那时我打破原则,不顾道德问题而前往尼泊尔,那么为法服务的纯净,将开始被污染,而这污染也会如箭般的终生刺着我。
时机成熟后,不需欺骗我就可去尼泊尔传法,同时法的传递也如我老师所预期的。因此那时所做的抉择是一个好的抉择,一个法的抉择。